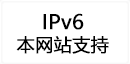第三期
- (卷首语)陈奎元为《科尔沁右翼前旗志》题词
- (特载)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领导和成员调整
- (特载)陈奎元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三届三次会议上得讲话
- (特载)陈进玉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三届三次会议上得讲话
- (特载)朱佳木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三届三次会议上得讲话
- (特载)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三届三次会议纪要
- (人才开发)内蒙古人才资源开发之浅见
- (考古探寻)内蒙古吐尔基山辽墓彩棺开棺纪实
- (文化天地)地方文献在内蒙古文化大区建设中的作用
- (文化天地)弘扬中华昭君文化探索品牌发展之路——对内蒙古昭君大酒店企业文化的调研与思考
- (文化天地)阿尔山的圣泉文化
- (史海钩沉)库图克台彻辰洪台吉事略
- (史海钩沉)用事实说话——日寇在王爷庙散播鼠疫纪实
- (历史一页)牙克石人民抵御外来侵略的故事
- (工作研究)我区首轮新方志编纂工作的基本经验
- (工作研究)关于地方志工作的思考
- (工作研究)县级方志资料建档工作之我见
- (续志时空)续志资料收集的必要与可行做法
- (方志书架)志苑春色入眼来
- (史志资料)1940年托克托县教育简况
- (史志资料)草原瓷都缸瓦窑
- (史志资料)喇嘛教的传入和曼楚克庙
- (方志巡礼)内蒙古新方志巡礼 (之十二)
- (专稿)向着太阳升起的东方——额济纳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笔记
- (珍珠滩)解读古城墙
- (珍珠滩)银肯响沙探秘
- (格言抄录)格言
- (珍珠滩)银肯响沙探秘
- 发布时间:2011-04-14
- 来源:本站原创
- 一、早春的响沙之歌
离开内蒙古包头,过了栏杆耀眼的黄河大桥,已近中午。
吉普车行驶在鄂尔多斯高原的柏油公路上。鱼米之乡大树湾和满城绿树的树林召都象画面一样在车窗外掠过。快到瓦窑汉墓群时,司机小赵把方向盘一转,车拐下西面一条辙印明显的土路。
“坐好! 车要跳迪斯科了!”话音未落,大家就像喝醉酒一样摇晃起来,车门剧烈地抖动着,人们的话音也连贯不起来了。好在时间不长,就进入一个开阔的河谷:好大的一个季节性内陆河床,东西足有100米宽,东岸岩壁陡立,西岸沙峰绵延。在塞外早春刚开始消融的罕台川冰道上行车,“嚓!嚓!”的冰裂声真叫人提心吊胆。
突然,车子一个右转弯,停在了月牙形的河湾边。“这就是库布其沙漠的响沙湾,西面这座海拔1150多米高的‘大骆驼沙’,就是我国的‘三大响沙’之一 ———银肯响沙。1991年国家已把这里辟为旅游点,你们是慕名而来的第一批。”原伊盟科委的乌农同志打开车门,指着左侧仰脖才能望见的大沙堤对我们说。
沙漠会唱歌的公开报道最初见于某通讯社的一位大惊小怪的记者。他在我国十二大沙漠之一的新疆塔克拉玛干随考察队采访,有一天晚间在百米左右的沙丘顶上宿营时,爬上沙丘猛然听到了“嗡嗡”的声音,一联想维吾尔语“塔克拉玛干”是“进去出不来”的意思,他就不由得紧张起来,以为是“幽灵之歌”。
其实,这就是“鸣沙”,又叫“响沙”、“哨沙”、“音乐沙”,是沙漠的一种奇异现象。我国的最早记载,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司马迁的《史记》,刘敬叔的《异苑》等都有描述。“丝绸之路”甘肃敦煌莫高窟附近的鸣沙山,响声如滚滚车轮,又如“八面埋伏”的琵琶古乐,乃自古“沙岭晴鸣”的“敦煌八景”之一。包兰铁路必经的宁夏中卫沙坡头号称“世界沙都”,附近的响沙高120米,殷殷作响时,声似鼓角相闻,深沉幽远。
银肯响沙的声音又是怎样的呢? 我顾不上疲劳,兴致勃勃地向沙丘走去。它面向东南,坡长100多米,高60多米。手脚并用才攀登得快些,我一口气爬上了十几米。听听吧!下滑至底居然毫无声响,这是怎么回事?
“来得不是时候,老郝同志!”乌农对我说:“每年五月至十月,阳光近乎垂直照射,沙子热得烫手的时候才有希望听见响声哪。现在地没解冻冰没消,你就想听沙漠唱歌,没门儿!”
果真如此吗?我不甘心。一边向月牙湾的北侧中心移动,一边用手刨沙,依然没有反响。正在我快失望时,指缝间忽然“嗡”的一声,吓了我一大跳。有第一声就有第二声,我双手拼命刨起来,“嗡嗡”变成了“轰轰”,琴声变成了雷鸣。我兴奋地大喊“响了!响了!”,使足力气第二次向沙堤中部冲去……
这回我如愿以偿了:象汽车在身旁开动,象飞机在头顶盘旋,象《鄂尔多斯舞》的铜号在回荡,连绵不断的“轰轰”巨响伴着细沙粒的倾泻而下,把我一直送到沙丘脚下。
同行的另两位科学记者都一试为快,喜出望外,司机小赵也说不枉此行。我们3月4日的考察结论是:第一,象骆驼队一样的沙丘链只有与月牙形河床平行的八十多米的一段才有沙鸣现象,其余沙丘形状相似,但与音乐无缘。第二,“银肯响沙早春不唱”的定论有待进一步验证。
二、 一个悲壮的传说
在直奔伊盟盟府东胜的路上,乌农给我们讲了一个令人难忘的传说。它是这样的悲壮激越。
原来,古代的银肯湾是罕台川畔的宗教中心,一座金碧辉煌的喇嘛教召庙远近有名。鄂尔多斯王爷驱使奴隶苦干了三年建起这座召,由于全国只有西藏的布达拉宫才可以与它媲美,因此号称“东藏”。召里有经堂七七四百九十间,有大小喇嘛九九八百一十个。庙会时煮“胡里尔巴达”(肉粥)的曼经锅比房子还大,跳鬼时念经的铜号有十来丈长。
可恨大喇嘛荒淫无道,残暴成性,不但百般虐待召庙中地位低下的小喇嘛,逼他们饿着肚子割草,顶着风雪砍柴,任意鞭打;而且嗜吃人肉,手段残忍。一个小喇嘛跳鬼节时冻得手抖,在曼经锅边搅饭时动作慢了一点,让他看见,一巴掌打进锅内活活煮死熬了肉粥。其他小喇嘛清洗大锅时发现锅底有小孩指甲,才明白同伴已残遭暗算。
铜号震天,怒火填膺,小喇嘛们忍无可忍揭竿而起了!他们捣经堂,烧召庙,与大喇嘛展开了殊死搏斗,大喇嘛临死前使出“杀手锏”镇压了起义,但奴隶们的呐喊声、铜号声常常冲出沙层。
乌农对我们说,清代,鄂尔多斯达拉特旗优秀蒙古族儿女组成的反清灭洋抗垦组织“独贵龙”,就以“银肯湾”为根据地拉起了民族民主革命的大旗。到今天,独贵龙歌曲《银肯敖包》还在广为流传。歌词中的“六十个好”既赞扬草场好、独贵龙将士好,也赞扬革命根据地———银肯响沙好!
三、“静电说”与“共鸣论”
响沙之谜引起了众多科学家的兴趣。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祯,1959年他七十高龄参加野外考察时,曾以浓厚的兴趣爬上宁夏中卫的沙丘下滑,作响沙的实验。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女教授李孝芳在新疆等地考察沙漠后,在1962年5月出版的《我国的沙漠》中宣称:神奇的“沙鸣”现象“已经为近代科学打破了,这种声音原来是一种极为干燥并且带电的沙粒,在外力作用下,彼此冲撞摩擦所发出来的”。持同观点的美国珀杜大学地貌学家梅尔霍恩在美国《80年代的科学》上撰文报告说:“常常有这种情况,即一切条件似乎都具备了却不会产生这种音乐。”
李孝芳教授曾经对内蒙古一位年轻的科研工作者的“特殊共鸣箱”理论感兴趣,笔者曾见过她的亲笔信。在她推荐下,《地理知识》以“响沙”为题报道了内蒙古学者介绍银肯响沙的文章。他认为沙丘下面存在的潮湿的沙土层和罕台川水汽蒸腾形成的“墙”构成了银肯响沙的“特殊共鸣箱”。我们在东胜拜访他时,他还满自信地告诉我们,160平方公里的库布其沙漠中只有罕台川畔的银肯湾具备了“特殊共鸣箱”的苛刻条件,别的类似沙丘不响;这个沙丘离开了这个特定的地点也不响。一位日本科学家曾经让响沙搬到他们后花园唱歌,结果一挪地方就哑了,纯属异想天开!
四、三个记者的发现
3月7日夜,在鄂尔多斯我们做出了如下决定:仿照美国得克萨斯大学林赛教授工作组的方法,把银肯响沙的“歌声”录下来;移开当地响不响,也要亲自试一试。
3月8日上午11时,我们三人又来到银肯响沙,虽然大河槽里北风呼呼,沙粒打在脸上生疼,但响沙依然用殷殷如雷的歌声迎接了我们。当我和《深圳商报》主任记者田文仲在沙丘底部搞移动试验的时候,青岛出版杜总编徐诚和伊盟的林业工程师吴健雄提着录音机一口气爬上了银肯响沙的顶部。发现60米高的银肯沙主峰背后是一望无际的复合沙丘,小沙丘居然都能唱歌。他们把沿途所见所闻都录了音。
响沙离开大沙丘1米、2米、5米,都照响不误:不过不是林赛教授他们的办法———“把沙子堆起来,然后再把它们推开”,而是把沙子摊开,用力向中心挤压、每次都“嗡嗡”作响。
当天下午2时35分,我们随车携带的银肯沙在黄河大桥上试验,响了。3时50分,包头火车站门前,响了。晚8时30分,呼和浩特内蒙古日报社家属房,响了。第二天中午依然响。三个多月后的6月11日下午7时,当众表演依然响!
我们三人共同认为:响沙离开当地特殊地貌、地质环境居然“歌喉依旧”是新的发现,异地保持“歌喉”三个多月也是史无前例的。
五、待突破的世界难题
沙漠发声的现象在地球上已存在许多世纪了,除我国外,中东国家在六世纪就有这方面的记载。在贝鲁特的一个山洞里,人们把这种声音比作打手鼓的声音;在西奈,作家感到这种声音象是远方的大炮在轰鸣或是从一个风琴里发出的深沉音调。美国内华达沙漠里的“石英沙歌唱”时,“象一把低音提琴的音响,有时象一只雄猫在栅栏上叫唤”。而新近发现的美国下加里福尼亚的贝尔山,沙地发出的声音就像“用手指摩擦玻璃杯的边一样”。除沙漠地区外,海滩、湖滨也不乏其例。与夏威夷的檀香山相隔120公里的考爱岛的海滨附近,有一座长800米、宽18米的沙丘,人在沙丘上行走,也会听到“类似狗叫的声音”。
各国科学家都觉得这是个谜。至今,静电摩擦、石英共振、空穴来风、音箱共鸣等都不能算是完满的解释。
偌多的沙漠,何以只有几处沙鸣? 显然特定的地质、地貌、沙粒特性、均匀度、水文条件关系极大。海滩、湖滨有水渗入自不必说,我国三大响沙脚下都有泉水、河水,且都特具月牙形状,是不是一个共性?
银肯响沙迁移他处照响不误显然比日本响沙高出一筹,但只拿静电摩擦能说明吗?银肯湾相邻相似的沙坨有的是,只有月牙形的一处能唱歌,离开地域的特殊性无法解释。但该处的响沙挪了地方照样响,说明特性得到保持且三月无妨,这是电性呢?还是磁性?还是电磁感应?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世界难题———响沙之谜啊,谁能倚天抽剑,首先突破呢? 原载《旅游》1999年第1期,征得作者同意,现予以发表。(作者单位:内蒙古沙产业、草产业协会副会长兼 秘书长《政协经济论坛》执行主编)
- 年鉴刊物上一篇:(工作研究)县级方志资料建档工作之我见
- 年鉴刊物下一篇:(工作研究)关于地方志工作的思考
- 声明: 转载请注明来源于《内蒙古区情网》官方网站














 当前位置:
当前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