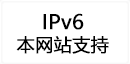第六期
- (卷首语)战士的心——献给书写史志的人们
- (志鉴论坛)论方志术语建设
- (志鉴论坛)志书编写一定要注意前后一致
- (志鉴论坛)修志必须以档案等史实资料为基础——兼评《突泉县志》(1986~2005年)
- (工作研究)坚持科学发展观实现地方志事业又好又快发展
- (工作研究)强化管理职能创新服务机制为自治区党政机关提供有力保障
- (专 稿)对草原文化艺术活力的跨文化解读
- (专 稿)奥运冠军草原来
- (史海钩沉)老庄与道 (七)
- (史海钩沉)绥远城清代碑刻辑录考述
- (史海钩沉)佛教文化在克什克腾旗的历史见证
- (学术探讨)匈奴民歌是地地道道的阴山之歌
- (桑梓英才)奈曼旗文化名人述略
- (人物剪影)奥登高娃:用歌声传播文化
- (方言丛谈)包头方言探微之一
- (蒙名选译)蒙古族蒙古语人名音意蒙汉文对照(十三)
- (文化博览)国名由来
- (大事记)世界大事扫描(2009年11~12月)
- (大事记)中国大事概览(2009年11~12月)
- (大事记)内蒙古大事记(2009年11~12月)
- (珍珠滩)重游白塔随感
- (珍珠滩)神奇的乌湖克图
- (珍珠滩)北疆恋歌(散文诗一束)
- (史海钩沉)老庄与道 (七)
- 发布时间:2011-04-14
- 来源:本站原创
老庄的贵身、尊生哲学,是在乱世中求生存的方法。在那个诸侯混战,兼并盛行,“以百姓为刍狗”的时代,隐居不仕是他们反对暴政的唯一选择。然而庄子的遁世,不同于普通的隐居山林,与世隔绝,庄子的隐是“德隐”而非身隐。他在《缮性》篇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世丧道矣,道丧世矣,世与道交相丧也。道之人何由兴乎世,世亦何由兴乎道哉!道无以兴乎世,世无以兴乎道,虽圣人不在山中,其德隐矣。隐,故不自隐。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仕与不仕,要看时势能否“兴道”,不考虑个人名利,这就是圣人与凡夫俗子的本质区别。所以,庄子对穷通的理解与世俗迥然不同。他引用孔子的话来表达:“我讳穷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时也。当尧舜而天下无穷人(不得志之人),非知得也;当桀纣而天下无通人,非知失也。时势适然。”(《庄子·秋水》)庄子对穷通的态度是:古之得道者,穷亦乐,通亦乐,所乐非穷通也。道得于此,则穷通为寒暑风雨之序矣。(《庄子》.让王)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老庄的人生哲学概括为两句话:外则贵身以自存,内则养生以自乐。因为贵身,所以尊生;因为尊生,所以养生;尊生有道,养生有术。
庄子所谓的养生之术,实质上是养生心之法。庄子在《在宥》篇中记载了黄帝与广成子的一段对话:黄帝问广成子:“治身奈何而可以长久?”广成子说:“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心静必清,无劳女(汝)形,无摇女精,乃可以长生。”所谓无视无听,是说要正视听,耳不乱于五音,目不迷于五色,心如止水,神形不亏,就可以长寿。养心之法的关键是心静:“圣人之静也,非曰静也善,故静也。万物无足以铙心者,故静也。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庄子·天道》)要保持心静,就要排除私心杂念,涵养正气:“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心正则平易,“平易则恬淡矣。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其德全而神不亏。”庄子认为,虚无恬淡,是天地的准则,道德的实质。而多欲妄求,是违背养生之道的。“虚无恬淡,乃合天德,…悲乐者,德之邪也;喜怒者,道之过也;好恶者,德之失也。故心不忧乐,德之至也;一而不变,静之至也;无所与忤,虚之至也;不与物交,淡之至也;无所于逆,粹之至也。故曰:形劳而不休则弊,静一而不变,淡而无为,动而以天行,此养神之道也。”(《庄子·刻意》)恬淡无为,不是说什么事都不做,而是不任意妄为。所谓“动而以天行”,就是说行为要符合做人的道德,不违法悖理。圣人的行为是“感而后应,迫而后动,不得已而后起。”看似被动,实则以静制动,动则必得。因事而起,事已复归平静,一如水的品性。
富贵权势享乐,是世人的共同追求,“心不待学而乐之,体不待象而安之。”孰不知大富有大忧,大贵有大害。基于这样的认识,庄子提出“平为福”的观点。什么叫“平”?庄子认为,不足而求之,不为贪;有余而不辞,是为贪。人对名利的追求以适度为限,适度就是平,过度就是不平,“有余为害者,物莫不然,而财其甚者也。今富人,耳营钟鼓管籥之声,口嗛于刍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遗忘其业,可谓乱矣;侅溺于冯气,若负重行而上阪,可谓苦矣;贪财而取慰,贪权而取竭,静居则溺,体泽则冯,可谓疾矣;为欲富就利,故满若堵耳而不知避,且冯而不舍,可谓辱矣;财积而无用,服膺而不舍,满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谓忧矣;内则疑劫请之贼,外则畏寇盗之害,内周楼疏,外不敢独行,可谓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遗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尽性竭财,单以反一日之无故而不可得也。”(《庄子·盗跖》)利欲熏心的人,享其乐而忘其忧,求其利而忘其害,贪求不止,轻则损害健康,重则搭上性命。大难临头,欲为平民以生而不可得,这样的悲剧不胜枚举。庄子的话好比暮鼓晨钟,振聋发瞶,而追名逐利之人早已目盲耳聋,听不到这些警世之言。庄子在《大宗师》篇中提出一个耐人寻味的命题:“杀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什么意思?所谓杀生就是能俭,即诸葛亮在诚子训言中说的“俭以养德,静以修身”之意。饮食男女,人之性也,饥而食,寒而衣,成年择偶为夫妻;耕有田,织有机,三间房屋可栖息。如此而已。能知足而止,心无妄求,即为杀生,即为守俭,这才是养生之正经,这样的人才可能终生无害,终其天年。不死者,不死于祸患之谓也。所谓生生,就是穷奢极欲,锦衣玉食,声色犬马,朝欢暮乐,嘻游无度,自以为快乐,实则灭性害生,即使无外来祸患,也足以折其寿命。《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就是例证。所以说生生者不生。“嗜欲深者,其天机浅。”天机就是聪明,沉溺于淫乐之中的人,如同行尸走肉,失去了理性,分不清利害祸福,是另类的自杀。
在老庄看来,所谓得道之人,就是懂得养生之道的人。“啮缺问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视,天和将至;摄汝知,一汝度,神将来舍。德将为汝美,道将为汝居。”(《庄子·知北游》)道德依归于心静神全的人,只有不受名利与淫欲的诱惑,保持赤子之心,才会脱离世间之苦。老庄深知虚伪的危害,提出贵真的思想:“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其用于人理也,事亲则慈孝,事君则忠贞,饮洒则欢乐,处丧则悲哀。…事亲以适,不论所以矣;饮洒以乐,不选其具矣;处丧以哀,无问其礼矣。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愚者反此。…禄禄而受变于俗,故不足。”(《庄子·渔父》)由此可见。庄子并不否认忠孝观念。也没有摈弃人伦世情,他反对的是虚伪做作、违真矫情的世俗习惯,强调发自内心的喜怒哀乐、亲情友情,社会充满真情,才会有真正的和谐与美好。
五、老庄学说对后世的影响
中国古代出了两位圣人,一位是老聃,另一位是孔丘。老子是出世的圣人,孔子是入世的圣人。据说孔子曾拜老子为师,但二人的学说大相径庭,格格不入。汉武帝之后,被董仲舒加工后的儒家几乎一统天下,但老庄学说的某些内容,仍是统治者不可或缺的理论武器。他们的思想是历代士大夫做官修身的智慧源泉,更是正直之士的精神寄托,许多大学者、思想家从老庄的著作中汲取营养,受到启迪。
成书于西汉初年的《管子》一书,既有“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儒家理论,也有老子清静安民的思想反映:“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安存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故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管子》牧民)与“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看法如出一辙。“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如天如地,何私何亲;如月如日,唯君之节。”(出处同上)这一段话是《老子》“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的翻版。两种表述,一个意思,是说一家之主,就要为全家人谋利益;一乡之长,就要为全乡人谋利益,以此类推。如果怀着一家之私念去作乡长,或者身为国君,却只为自己身边的人办事,那么这个乡这个国是肯定治理不好的。《管子·乘马》篇中说:“无为者帝,为而无以为者王,为而不贵者霸。”显然是脱胎于《老子》一书。
我国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所著《韩非子》,将老子道的观念引入法家的理论:“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故虚静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者正。有言者自为名,有事者自为形,形名参同,君乃无事焉,归之其情。故曰:君无见其所欲,君见其所欲,臣自将雕琢;君无见其意,君见其意,臣将自表异。故曰:去好去恶,臣乃见素;去贤去智,臣乃自备。故有智而不以虑,使万物知其处;有行而不以贤,观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群臣尽其武。…明君无为于上,群臣悚惧乎下。臣有其劳,而君有其功…人主之道,静退以为宝。不自操事而知拙与巧,不自计虑而知福与咎。”(《韩非子·主道》)此外,韩非还有“解老”、“喻老”二篇,前者对《老子》书中难明之义进行解释,后者是以事例说明老子的观点。
秦国宰相吕不韦与门客撰著的《吕氏春秋》以道家的思想开篇立论,如第一篇《本生》:“始生之者,天也;养成之者,人也。能养天之所生而勿撄之谓天子。夫水之性清,土者抇之,故不得清。人之性寿,物者汩之,故不得寿。物也者,所以养性也,非(所)以性养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养物,则不知轻重也。若此则每动无不败,以此为君悖,以此为臣乱,以此为子狂。…贵富而不知道,适足以为患,不如贫贱。故古之人有不肯富者矣,由重生故也,非夸以名也,为其实也。”接下来的《重己》篇说:“今吾生之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论其贵贱,爵为天子,不足以比焉;论其轻重,富为天下,不可以易之;论其安危,一曙失之,终身不复得。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天下,重物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于它物乎?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可以托天下。”(《吕氏春秋·贵生》)这番议论完全由庄老外物重生的思想而来。庄子养生的思想在《吕氏春秋》中也有反映:“天生阴阳寒暑燥湿,四时之化,万物之变,莫不为利,莫不为害。圣人察阴阳之宜。辩万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寿得长焉,长也者,非短而续之也,毕其数也。毕数之务,在乎去害。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咸,五者充形则生害矣。大喜、大怒、大忧、大恐、大哀,五者接神则生害矣。大寒、大热、大燥、大湿、大风、大霖、大雾,七者动精则生害矣。故凡养生,莫若知本,知本则疾无由至矣。”(《吕氏春秋·尽数》)这段话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叫做毕数或尽数。老庄讲养生和长生,并没有“长生不老”的意思,所谓长生是指能终其天年,不中途夭折。即《尚书·洪范》中说的“考终命。”老子曾说“死而不亡者寿,”从未讲过人可以不死的话。后来的道教把长生解释为不死,完全歪曲了老子的本意。《吕氏春秋》的毕数(尽数)说,继承了“考终命”的思想,对养生的目标予以明确。是很有意义的。人生各有寿数,趋利避害,安神保形,使自己活到应有的岁数,这就是善养生,就是福分。
(作者: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调研室)
- 年鉴刊物上一篇:(大事记)内蒙古大事记(2009年11~12月)
- 年鉴刊物下一篇:(专 稿)奥运冠军草原来
- 声明: 转载请注明来源于《内蒙古区情网》官方网站














 当前位置:
当前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