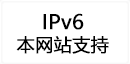第六期
- (卷首语)战士的心——献给书写史志的人们
- (志鉴论坛)论方志术语建设
- (志鉴论坛)志书编写一定要注意前后一致
- (志鉴论坛)修志必须以档案等史实资料为基础——兼评《突泉县志》(1986~2005年)
- (工作研究)坚持科学发展观实现地方志事业又好又快发展
- (工作研究)强化管理职能创新服务机制为自治区党政机关提供有力保障
- (专 稿)对草原文化艺术活力的跨文化解读
- (专 稿)奥运冠军草原来
- (史海钩沉)老庄与道 (七)
- (史海钩沉)绥远城清代碑刻辑录考述
- (史海钩沉)佛教文化在克什克腾旗的历史见证
- (学术探讨)匈奴民歌是地地道道的阴山之歌
- (桑梓英才)奈曼旗文化名人述略
- (人物剪影)奥登高娃:用歌声传播文化
- (方言丛谈)包头方言探微之一
- (蒙名选译)蒙古族蒙古语人名音意蒙汉文对照(十三)
- (文化博览)国名由来
- (大事记)世界大事扫描(2009年11~12月)
- (大事记)中国大事概览(2009年11~12月)
- (大事记)内蒙古大事记(2009年11~12月)
- (珍珠滩)重游白塔随感
- (珍珠滩)神奇的乌湖克图
- (珍珠滩)北疆恋歌(散文诗一束)
- (学术探讨)匈奴民歌是地地道道的阴山之歌
- 发布时间:2011-04-14
- 来源:本站原创
匈奴是中国古代北方的一个游牧部族,兴起于公元前三世纪(战国时期),衰落于公元一世纪(东汉初)。曾在蒙古高原上的大漠南北活跃了约三百年,其后又在中原地区活跃了约二百年。它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都发生过较大的影响。
匈奴人无文字。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但究属该系中的蒙古语族,抑属突厥语族,至今尚无定论。匈奴人创造了辉煌的青铜文化。他们虽无文字,但民歌却很优美动听。至今流传下来的文字遗产不多,仅有一首民歌而已。
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失我焉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
这首匈奴民歌刊载于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历代少数民族诗词曲选》第一页上。它千百年来广为流传,许多人耳熟能详,但是由于对它一直有种种不同的解释,以致使它失去了本意。现在到了应该为它正本清源、去伪存真的时候了。
匈奴民歌是怎样流传下来的,其注解源于何处?
翻开《史记·匈奴列传》,其中有一段如下记载:“其明年春,汉使骠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击匈奴,得胡首虏(骑)万八千余级,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骠骑将军复与合骑侯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两千里,击匈奴。过居延,攻祁连山,(四)得胡首虏三万余人,裨小王以下七十余人。”
(一)括地志云:“焉支山一名删丹山,在甘州删丹县东南五十里。《西河故事》云:“匈奴失祁连、焉支二山,乃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其憋息如此。
(四)索隐按:《西河旧事》云“山在张掖、酒泉二界上,东西二百余里,南北百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温夏凉,宜畜牧。匈奴失二山,乃歌云‘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祁连一名天山,亦曰白山也。
上述《史记·匈奴列传》中的记事及其两个注解,记载了这首匈奴民歌,并因此使它流传于后世。
陇右、河西并非匈奴故地
匈奴民歌中所说的二山,均在今甘肃西部河西走廊,即《史记》中所说的陇右。当时这个地区原为月氏(音肉支)族世居游牧地。匈奴第一代单于头曼时代,月氏族势力强大,控弦十余万骑,对匈奴造成直接威胁。头曼单于为了保境睦邻,曾将长子冒顿(音墨毒)送往月氏以为人质。并拟发兵袭击月氏,假月氏之手,除掉人质,以实现废嫡立庶之计。冒顿没有听任命运的摆布,盗得月氏王的良马,星夜奔回匈奴。头曼单于嘉其壮,命其任万骑长。其后冒顿利用自创鸣镝(响箭),培训出一支绝对听命的铁骑兵,然后杀父自立为单于。后经几年秣马厉兵,励精图治,一举破灭东胡;公元前206年,西向击走月氏。月氏向西北远迁伊犁河谷者称大月氏,其余进入祁连山区与羌族杂居者称小月氏,与邻境其他20余种羌族共同服属匈奴。匈奴伊稚斜单于时,河西走廊西半部为浑(昆)邪王所居,东半部为休屠王所居。
从汉匈两次战争结果可知,陇右不是匈奴民歌的诞生地
西汉至高祖到武帝约60年间,一直采取和平外交政策,边境基本相安无事,因此,国内经济不断发展,社会财富渐增,军事实力加强。从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到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十年间对匈奴发动了九次大远征。
汉武帝元狩二年,匈奴伊稚斜单于六年(公元前121年),春三月,汉遣骠骑将军霍去病将万骑,由陇西郡出国境袭击匈奴,在匈奴防军顽强抵抗下,步步推进,历五王辖区,转战六日,越过焉支山千余里,至酒泉附近结束战斗。
此役汉军大胜,杀二王(折兰王、卢胡王),斩首八千九百余级,收休屠王祭天金人。此役为汉朝对匈奴发动的第七次大远征。
夏,霍去病与合骑侯公孙敖将数万骑出北地,向西北推进到居延海(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噶顺诺尔)时,突转南下,在今酒泉附近,横跨甘、青两省交界的祁连山区,完成对匈奴的围歼。得匈奴单(音善)桓、酋凃王及相国、都尉以众归附者两千五百余人以及单于的阏氏(夫人)。
汉军春夏两次长途奔袭匈奴右部,战果辉煌,凯旋。
秋,匈奴伊稚斜单于对右部浑邪王及休屠王在西方战败,被汉军杀掠数万人,极为恼火,欲召诛之。浑邪与休屠二王惧怕追究战败责任,共谋降汉,以避其祸。旋休屠王反悔,浑邪王袭而杀之,遂合并两部之众四万余人,开赴长安,降附汉朝。汉封浑邪王为漯阴侯,又封其裨王呼毒尼、仆多、乌犁、稠雕四人为列侯。
汉朝遂将匈奴降众分徙西北边境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等五郡故塞外,成立五属国予以安置。自此,金城河(黄河上游今兰州以西一段)西傍南山至盐泽(今新疆罗布泊)空无匈奴。匈奴虽有斥候到达,但为数以稀。(1)
当时河西以至罗布泊既然空无匈奴,甚至连匈奴的侦查兵也很少见,可见这个地区基本上已成渺无人烟之地。大约六年之后,即汉武帝元鼎二年,汉乃于浑邪王故地置酒泉郡,后于休屠王故地置武威郡,徙民充实之,以绝匈奴与羌族交通之路。据此可知,河西既然没有匈奴人民,怎么会有匈奴民歌?上述无可争辩的事实,说明了陇右、河西不是匈奴民歌的诞生地。那么匈奴民歌究竟诞生于何处?
匈奴民歌源于阴山
这首民歌的特点是:语言简练,含义深刻,仅有两句话,几十个字,后一句又是前一句的重叠和加深。歌中所说匈奴失掉两座山,实际上匈奴失掉的只是一座山,那就是阴山。上句为密切结合生产和生活的现实,而抒发出人民的喜怒哀乐。阴山失守了,匈奴人民面对着由于山川草原的丧失而引起畜牧业衰落的现实,发出了内心的哀怨;下句是上句的叠唱和深化,完全是民歌的特色。上句的祁连山,实际就是阴山。内蒙古博物馆收藏的甸城碑记有“郡北一舍,有环绕之山,名曰祁连”的记载。清人张鹏翮在《出塞纪略》中说:“(离归化城)北行九里,入祁连山(此山亦名祁连,非《元和郡县志》甘、伊西诸州之祁连山也。)”据此可知,阴山又称祁连山。则历来把《匈奴民歌》里所说的祁连山、焉支山指为阴山以外的什么山的说法,都是失误的。
蒙古族史学家陶克涛先生认为,祁连一词,应当是匈奴语的译音,与今蒙古语的蒙文一词音似,意为湿润的原野;焉支亦为匈奴语,于今蒙古语的蒙文一词音似,意为母亲(匈奴称夫人为阏氏,而母阏氏,即母亲)。如果把这首民歌重译成明白的汉语,应当是这样的:
失去我们湿润的原野之山,
牲畜不能在这里繁殖了;
失去我们母亲似的这个山野,
妇女们悲伤地不成样子了。
这首民歌的词义所指,都是匈奴人民对阴山的怀念和爱恋。(2)
匈奴语“祁连”是匈奴人对阴山的称呼,意为湿润的原野之山,事实上,阴山的自然条件和这个称呼是名副其实的。至于匈奴人又把阴山称作“阏氏山”是因为阴山、河套曾经是匈奴民族的摇篮,他们是在阴山湿润的原野上,成长壮大起来的,所以匈奴人又把阴山,称为“母亲山”。
钟敬文教授说:“歌谣,是人民自己创作和保存的文学。在这种文学里,固然反映出人民的日常生活和他们对于这种生活的思想、感情,同时更反映出社会、民族的重大事件,反映出人民对于这种事件的态度、心情。”(3)
匈奴民歌所反映的社会、民族的重大事件,就是匈奴民族失掉了阴山牧场,影响了畜牧业的繁殖。这个事件的严重后果,有可能置匈奴民族与死地。因为匈奴是个游牧民族,社会财富的积累和人民的衣食来源,主要依靠畜牧业生产提供。丢掉了牧场,六畜不能繁殖,整个民族的生机就有被扼杀、断送的危险。而匈奴人民怎能不为此焦虑、叹息,以至于愁苦不堪呢!匈奴人民为什么对阴山牧场,如此怀念和爱恋?因为,阴山不是普通的牧场。《史记·匈奴列传》说:匈奴“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都没有离开阴山河套(包括鄂尔多斯高原),可以说阴山河套是匈奴民族成长的摇篮。《汉书·匈奴传》说:“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音墨毒)单于依阻其中;制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阴山对于匈奴民族的重要性于此可见。它既是林草丰茂的优良牧场,又是御敌自卫的天然屏障和战略要地。
匈奴失阴山,应该是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春,汉朝向匈奴发动第九次大远征之后。当时卫青统帅四个将军、五万精骑兵出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直趋漠北,迎战单于亲卫军。霍去病率五万骑兵出代郡(郡治在今河北蔚县附近),向北进军。此外,从民间征调担任补充战马、运输辎重的私负从马十四万匹,另有步兵及后勤部队数十万人,踵随其后。汉军实行“绝漠”会攻,企图一举而服匈奴。而匈奴统治者则用“诱敌深入”的战略,把精兵列阵于漠北,以逸待劳,迎战汉军。卫青大军进至漠北,两军相遇,展开激战。汉军以武钢车(即有巾有盖、当作先驱用的战车),自环为营,阻挡匈奴骑兵的冲击,同时,纵五千骑截击匈奴。双方激战一日,互有伤亡。黄昏时大风骤起,飞沙走石,两军互不相见。卫青纵左右翼兵包抄匈奴单于,单于乃乘六骡、壮骑数百,突围向西北遁去。汉军斩首虏万九千余级,进至阗颜山(杭爱山)赵信城,得匈奴积粟,食军,然后放火烧毁余粟,扬兵而还。霍去病出塞两干余里,接战左贤王,左贤王败走,溃不成军,汉得首虏七万余级。汉军穷追至狼居胥山(克鲁伦河上游),“禅(祭地)于姑衍(山名),登临瀚海(今内蒙古呼伦湖贝尔湖,一说即今杭爱山的不同译音),表扬战绩,凯旋。”汉军虽大胜,但人马损失惨重。“是后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原来设立于阴山地区百余年来的“龙庭”,因战败,不得不远迁到漠北库伦(今乌兰巴托)附近。汉军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在今甘肃永登县西北),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然亦以马少,不复大出击匈奴。
由于千里阴山失守,所以班固在《汉书·匈奴传》中说:“边长老言,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后人也赋诗记其事说:“单于每向沙场猎,南望阴山哭始回。”读了新译匈奴民歌歌词,联系当时发生的历史事件,这首民歌所以诞生在阴山地区,并非偶然,是有其深刻地社会历史原因的。
匈奴民歌的旧译歌词,把上句和下句割裂开来,成了互不相干的两件事。上句说“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而下句却说“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这“六畜不蕃息”与“妇女无颜色”是互不相关的两件事,怎么能在一首民歌里出现呢?甚至有人望文生义,妄加解释说:“焉支山出产胭脂红,是妇女的化妆品,抹于口唇、指甲上,显得娇艳美丽,故单于的爱妻称‘阏氏’,是为燕支的同音异议,后来汉人学了匈奴人的风俗,才利用‘胭脂’二字,可知古代妇女抹红,是从匈奴民族开始的。”(4)这种解释与上句的“六畜不蕃息”实在相去甚远,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如果承认旧译为合理,继续沿用旧译而不予改变,首先这完全不符合民歌的体例。
民歌的反复、重叠手法的经常使用,也是民歌的一个重要的特点。英国一名著名的作曲家在谈到民歌时说:“我们往往觉得有些音乐初听似乎很动听,但是一经重复便索然无味了。民歌的妙处却必须重复几遍,才显得出来。”可见重复正是民歌不同于其它音乐的地方。歌词也是如此。有些民歌歌词整段只换了几个字,然后反复的唱。民歌反复重叠的手法,也是自古就有的。《诗经》中使用反复重叠的歌词就很多。例如卫风《木瓜》:
投我以木瓜,报之于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送我一个木瓜,我送琼琚给她。不是作为报答,只为想娶她。)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送我一个木桃,我送美玉琼瑶。不是作为报答,只为永远相好。)
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用以为好也。(赠我一个木李,我送琼玖为礼。不是作为报答,只为永不离弃。)
口头文学中常常使用反复重叠,除了我们上面所说的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了便于记忆和念来顺口。这种例子在蒙古民歌中也有很多。例如《伊敏河》:
伊敏河上的激流漩涡,飞溅着耀眼的金色浪花;年迈的阿爸额吉,令我每时每刻在牵挂。
伊敏河上的激流漩涡,飞溅着耀眼的银色浪花;年迈的阿爸额吉,令我每日每夜在牵挂。
民歌中字和词的重叠使用,可以使歌词音节铿锵和谐,可以加强语音的明确性,使语音更富有表现力。
民歌的概括和它语音的洗炼性是分不开的。一般的民歌,都是形式精短,但概括的内容却往往极其丰富,这是和民歌的口头流传的特质直接有关的。民歌总是真挚、热情地表达出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这是民歌所以动人的地方。
民歌的上述特点,在匈奴民歌中也有着鲜明、突出的体现。
最后应该特别指出的,就是匈奴民歌中,上句说:失去我们湿润的原野之山,牲畜不能在这里繁殖了;而下句则说:失去我们的母亲似的这个山野,妇女们悲伤地不成样子了。为什么要强调“妇女们悲伤地不成样子了?”这只能从匈奴的游牧生活中男女不同的社会分工去理解,才能够明白妇女们最为悲伤的原因。因为匈奴是游牧社会,男女分工不同。男子主要习武打仗,而牲畜的饲养管理以及家务劳动,全由妇女们承担。当牲畜赖以生存的山川草原丢失之后,最感到悲伤难过的当然也就是妇女们了。
注:
(1)《匈奴历史年表》25、26页,林斡著,中华书局,1984年,北京
(2)《毡乡春秋》263页,陶克涛著,人民出版社,1987年,北京
(3)钟敬文:《民间歌谣中的反美帝意识》载《民间文学集刊》第二册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0年,北京
(4)《长城话古》80页,陆思贤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呼和浩特
(作者:内蒙古地方志办公室)
- 年鉴刊物上一篇:(珍珠滩)北疆恋歌(散文诗一束)
- 年鉴刊物下一篇:(珍珠滩)神奇的乌湖克图
- 声明: 转载请注明来源于《内蒙古区情网》官方网站














 当前位置:
当前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