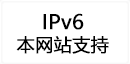第一期
- (卷首语)提高水准 展现风格
- (特载)在会见全国地方志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代表时得讲话
- (志鉴论坛)试论地方志书述而不作
- (志鉴论坛)关于新编地方志书“序”的探讨
- (志鉴论坛)续志应注重对静态事物的记述
- (专稿)昭君出塞热两千年不衰说明什么
- (专稿)元朝南北大统一与元上都经济文化的空前发展
- (专稿)话说礼教
- (文史博览)浅谈乌兰毛都草原文化地域化
- (文史博览)一段段串话夸莜面
- (文史博览)话说丰镇月饼
- (文史博览)内蒙古的地方戏——二人台
- (史海钩沉)中滩公社的1978
- (史海钩沉)绝世孤品
- (史海钩沉)木华黎——《李氏家谱》
- (人物剪影)回忆老旗长老盟长老主任色音巴雅尔同志
- (大事记)内蒙古大事记(2011年1~2月)
- (珍珠滩)踏访赵长城
- (珍珠滩)调寄临江仙
- (珍珠滩)春色迟来绿更浓
- (志鉴论坛)试论地方志书述而不作
- 发布时间:2011-12-28
- 来源:本站原创
提 要:第二轮修志的创新需求和途径均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对已有修志规范原则中不合理、不科学和与当今时代发展要求不相符合等因素的改进和完善,破除不合理的传统观念桎梏,寻求与时俱进的合理性创新发展。比如对述而不作这个通行志界的编纂原则,需要有更为深入的理解,完全意义上的述而不作不可能做到。志书中的“作”,可以理解为研究、编排和论证、论述、评论等。
关键词:地方志书 述而不作 编纂原则
地方志发展至今,在社会上不受重视的现象仍旧存在。究其原因,作为专业编纂、专门学问,地方志有其特定的流通和接受圈子。不仅方志如此,很多专门学科如历史学、文献学、语言学、逻辑学等都是如此,我们作为专业人员自可不必太过焦虑。但不可否认,方志自身发展存在问题,也是重要的原因。比如因编纂者,尤其是主编思想认识、知识水平、业务能力所限造成的志书内在品质不高,来自传统社会的志书形式与现代社会的不相适应,现行志书编纂思想和规范中尚有不完善、不合理的成分等等。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对待和加强第二轮修志工作”,“创新是一切学术性工作的生命,地方志工作同样要提倡与时俱进的精神,把方志办切实建设成为创新型方志办”①。
这里,特别需要处理好继承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做到有所因、有所创。前者是为传承优秀的地方志文化传统,后者则为保证地方志与时俱进地发展、永远生机勃勃。志书的创新,不是吸引眼球的矫情作秀、不是突发奇想的标新立异、不是不切实际的胡思乱想、不是一厢情愿的闭门造车,它必须具有理论支撑,经得起实践检验;必须具有普遍价值和意义,能够凭借卓有成效的实绩被人们广泛接受;必须符合方志发展的内在逻辑才能走出广阔的发展新路。第二轮修志的创新需求和途径均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对已有修志规范原则中不合理、不科学和与当今时代发展要求不相符合等因素的改进和完善,破除不合理的传统观念桎梏,寻求与时俱进的合理性创新发展。
志界现行的修志原则和编纂要求,或来自历史传统、或成于首轮修志,或为实践经验积累、或为理论提升结果,基本形成了属于方志学自己的规范,十分可喜。但是,如何避免简单化、片面化地理解这些原则和要求,如何理性地分析、思考、完善其中有待改进的方面,都是迫切需要认真思考和解决的问题。比如对志书资料性、述而不作,就存在简单片面的认识和操作。举例而言,在人们的议论中,志书缺乏观点、缺乏思想、缺乏内在逻辑关联的说法,是具有相当杀伤力的负面评价。志界一般都以志书是资料书、寓观点于资料之中、述而不作的方志编纂原则来作应对辩驳。对此,笔者觉得有必要作些分析。
志书坚持寓观点于资料之中的原则不容置疑,但有前提,这就是编纂者必须有“观点”,方能做到寓于资料之中。而“观点”来自思想,即编纂思想。编纂者必须有编纂思想,同样是不容置疑的原则。编纂者只有在明确了编纂思想后,才能用这个思想去消化、分析、甄别、研究资料,取舍、编排、组合资料,才能真正做到按志书体例要求,科学合理地、述而不作地、寓观点于资料之中地横分门类、纵述史实,编纂成志。要做到寓观点于资料之中,比“太史公曰”般地出面表达自己的观点难度更大,需要的是一种“大智若愚”的境界、“大道无形”的水平。
对述而不作的理解也是如此。事实上,完全意义上的述而不作是不可能做到的。“历史一词在中文、西文中都有两重内涵,一是常识意义上过去真实发生过的事情,或者说历史实在(His-torical Reality);再就是对这些事情的记载、考订、描述和解释。历史实在只能通过它留下的遗迹才能为人们所触及。历史学家所做的工作,就是针对这些遗迹的发现、搜集、考订、编排、解释和写作。可以说,人们总是通过历史学家所提供的第二重意义上的历史,来对第一重意义上的过去实在有所了解的。”②20世纪以来西方史学中渐次出现的重构论、建构论以及解构论,就是从第二重意义历史与第一重意义历史的关联、从历史学家通过史料来对历史实在所做工作的性质之角度,产生的三种不同的立场③。
笔者在此无意于详细介绍和探讨重构论、建构论、解构论的具体理论和方法,也并不试图将它们直接引入志书编纂中,只是在学习、阅读的过程中,联想到志界述而不作的说法,认为需要对述而不作这一志书编纂原则有更准确的认识和细致的辨析。具体到志书编纂而言,一方面,因为篇幅有限,浩如烟海的资料不可能全部入志,必定有一个选择、取舍的工作,入志资料必定是选择、组合的结果,也就是上面所说的“第二重历史”,其间自然就有编纂者的主观意识存在。也就是说,你遵循什么样的标准取舍编纂资料?你为什么“述”A而不“述”B?为什么甲事物详述而乙事物简述?为什么在此时此地“述”而不在彼时彼地“述”等等,都有一个比较选择的过程,都体现着编纂者的主观意图。因此,“作”是一个从本质上来说无法剔除的客观存在,不“作”即“述”,就有可能被动地陷入琐碎资料的海洋中难以自拔。另一方面,资料只有通过选择、组合才有意义,任何机械的、随意的、平铺直入的资料,是缺乏认知意义的,我们不能期望一堆自然状态存在的资料,会自然地向人们展示出其中的本质和意义。就像文学中的自然主义一样,即使你详尽到把文学人物脸上每一条皱纹都做了极其真实的描述,却忽视了人物典型性的塑造和性格特征的揭示,这种单纯客观主义描写的细节真实,只能称得上是表象的真实,因为泛滥的细节反而掩盖了本质的真实。建构论认为“历史学家的历史想象力、知人论世的愿望、对人性和世界运转方式的深入体悟”,对史家理解过去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志书品质的高低不一,确实与编纂者的认识水平、知识结构、生活阅历、人生感悟、综合能力等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在笔者看来,志书中的“作”,首先可以理解为“研究”,在志书编纂的全过程,编纂者都要充分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对本地地情、志书特征、编纂思想、编纂方法等问题认真分析探讨,出思想、出智慧、出观点、出结论,为志书的“述”打好扎实的思想基础。只有愿意“作”、主动“作”、认真“作”,同时又能“作”得准确、“作”得充分、“作”得深入的编纂者,才能真正“述”得有意义、“述”得有深度、“述”得有品质。其次,可以理解为“编排”,它广泛地存在于志书的篇目设计、内容选择和资料取舍中。科学合理的编纂设计和内容安排,可以为志书的“述”搭好坚实的记载框架和平台。再次,可以理解为“论”,如论证、论述、评论,即志书中分析、比较、综合的文字,发表的观点、见解、评价。志书不是学术论著,不是个人研究,但也不必因此绝对否定“论述”的存在。在全志的概述、综述,编下、章下的无题小序,大事记,尤其是专志、专题、专记、特记、附记、调研报告等记述形式中,都可以有“论”的位置。即使是在志文之中,基于充实资料之上的准确、恰当、点睛式的“精论”,也不妨尝试,以此加强志书的整体性,保持志书记述历史走向的完整性。
综上所述,对述而不作这个通行志界的编纂原则,需要有更为深入的理解,那种简单机械地编排大量从讲话、报告、总结、数据中抄引的资料,并将之视为述而不作的认识,是片面肤浅之见。正是这种不准确的片面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修志人员的思想和手脚,不敢投入情感、疏于深入思考、忽视分析研究、少有辨析比较,造成了入志资料和记述内容的单薄、平面和乏味。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志书编纂中,我们需要的是冷静、从容的态度和理性、睿智的文字,而非超然事外的漠然旁观、淡而无味的粘贴拼凑。述而不作并不等于貌似客观,实质不见思想智慧、没有灵魂的纯客观主义立场。资料性也好、述而不作也好,都不能成为编纂者不作思考、敷衍应对、盲目堆砌资料的借口;不能成为劣质志书疏于探究、懒于分析、就事论事、轻描淡写的自我辩解的托词;不能成为我们消极面对人们质疑志书价值的挡箭牌。
注释
①朱佳木:《在全国省级方志工作机构主任会议上的讲话》,《中国地方志》2010年第5期。
②彭刚:《历史事实与历史解释——20世纪西方史学理论视野下的考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③简单地说,重构论认为历史学的任务就是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建构论认为,重构论那种朴素的经验主义路数并不足以揭示过去的真实,历史学家也做不到像一面虚己以待的镜子那般的客观中立,历史学是对过往实在的表现或再度呈现,但此种表现地对象是已经消失、不在现场的东西。历史学家面对史料时,必定有所选择,而他的选择又会受到其价值观念、政治立场、个人气质、问题意识等各种交互缠绕的个人因素的影响。历史学家的历史想象力、知人论世的愿望、对人性和世界运转方式的深入体悟,对于史家理解过去具有重要意义。解构论认为历史学家无法直接面对过去,而总是通过各种史料来触及过去。各种形态的史料都是经人手制作而流传下来的过往的痕迹。历史研究依赖于此、并不断生产出各种文本。史料和史家工作产品的文本性,使得我们无从真正接触到过去。历史学研究的终极产品——历史学文本及其中所包含的历史解释——并不是对于过去的忠实再现。详见彭刚:《历史事实与历史解释——20世纪西方史学理论视野下的考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作者: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
- 年鉴刊物上一篇:(卷首语)提高水准 展现风格
- 年鉴刊物下一篇:(特载)在会见全国地方志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代表时得讲话
- 声明: 转载请注明来源于《内蒙古区情网》官方网站














 当前位置:
当前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