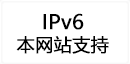第三期
- (卷首语)在抗震救灾中更深地显现出……
- (志鉴论坛)浅谈编修第二轮志书应着重把握的五个方面
- (志鉴论坛)续志应反映造城战略实施状况
- (专稿)内蒙古大学蒙古文学研究50年述评
- (专稿)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印刷企业的绿色视野——兼谈爱信达公司推动绿色印刷的基本策略
- (史海钩沉)强盗政治与名士风流——两晋历史三题
- (史海钩沉)清代右卫和绥远驻防城关系初探
- (史海钩沉)古城掘疑——吕布出生地暨九原郡考
- (史海钩沉)嘉庆年间马君选贩卖私盐案对阿拉善盐务影响
- (工作研究)学习、宣传、贯彻《地方志工作条例》,依法行政,全面提升兴安盟修志队伍的整体素质
- (工作研究)全社会重视支持努力做好锡盟第二轮地方志编修工作
- (民俗风情)蒙古族自然崇拜
- (文化博览)“香格里拉”释
- (文化博览)回族交际中的特殊词语及其文化含义
- (人物)耶律曷鲁 移剌窝斡
- (学习园地)学蒙古语
- (蒙名选译)蒙古族蒙古语人名音意蒙汉文对照(四)
- (大事记)内蒙古大事记(2008年5~6月)
- (珍珠滩)盛开的山丹花
- (珍珠滩)镂刻在生命中的记忆——写在母校50周年华诞之际
- (珍珠滩)抗震救灾——诗人的心声
- (珍珠滩)《金缕曲》抗震救灾
- (珍珠滩)《东风齐着力》救灾英雄赞
- (珍珠滩)和你在一起
- (史海钩沉)清代右卫和绥远驻防城关系初探
- 发布时间:2011-05-14
- 来源:本站原创
关于清代右卫八旗驻防城和绥远驻防城的关系,目前清史及满族史学界研究成果甚微,且这种关系是西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笔者主要根据《清实录》等史籍记载,对这两城的沿革关系及发展变化做一初步探讨,以期抛砖引玉。不妥之处,敬请专家指正。
一、右卫八旗驻防城设置的背景
清朝历任皇帝一再声称:“我国家以武功定天下”,表明了军事在他们建立政权和巩固统治方面所占据的极其重要的地位。所以,国家机器中军事职能的充分发挥,构成了有清一代政治统治的鲜明特点。我们知道,清朝入关后,各项制度多沿袭明朝旧制,惟有兵制创制兴革,这就是满族特有的八旗制度。这种制度不仅是军制,还是一个集行政、生产、军事诸职能为一体的社会组织形式。它形成了与历代汉族封建王朝兵制不同的种种特征。
八旗有禁旅和驻防之分。本着居重驭轻的原则,清廷将精锐旗兵集于京城,达十多万人,平时镇守党中央,有事调集出征。为便于对广大地区的控制,除设置绿营外,在水陆要冲还设置了十数万的驻防旗兵,这对地方起着巨大的震慑作用。这一独特的建立在民族和等级统治基础之上的制度,正是清廷用来镇压全国各族人民反抗以维护政治统治长达三百余年的最得力工具。
右卫八旗驻防城的设置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康熙十二年(1673年),吴三桂发动的“三藩之乱”爆发,清廷倾全国之力用八年时间将其削平,全国基本上又归于统一。从“三藩之乱”中清廷得到二点深刻的教训:一是“八旗满洲系国家根本”只有自己民族的武装才可真正信赖。康熙皇帝曾云:“凡地方有绿旗兵丁处,不可无满兵。满兵纵至粮缺,艰难困迫而死,断无二心。若绿旗兵丁,至粮绝少时或窘迫,即至怨愤作乱。”[1]二是为有效地控制全国,需在要害之地增设八旗驻防兵,从而形成一个控制和震慑地方的军事网络。这套八旗驻防军事体系,主要有三大部分。第一是沿长江、大运河、黄河、沿海地区的为防止汉族人反抗的驻防体系;第二是为对付蒙古族而于长城沿线设立的控制体系;第三是为防止沙俄扩张而在东北故里设置的驻防体系。基于以上两点认识,用八旗兵力量控制全国,已成为清廷的当务之急。
康熙中期,我国漠西蒙古准噶尔部兴起,在其首领噶尔丹的统领下,不断东进南下,进逼北京,最后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八月,清准双方爆发了“乌兰布通之战”。这标志着清廷的军事中心开始从内地转向北方地区。北京的重要性是众所周知的,从历史上看,将北京作为国都的明王朝,无不考虑它在防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方面的特殊位置。对清廷而言,蒙古稳定,可二者联合面对汉族的反抗,而无后顾之忧,一旦蒙古有变,从京城发兵进击,路途也不很远。所以,为京城安全计,从康熙初年,清廷陆续在其周围设立了喜峰口、独石口、古北口、罗文峪、三河、玉田、热河、张家口等小型八旗驻防点。为进击准噶尔蒙古部方便,在长城沿线设置大型八旗驻防城就提到了清廷的议事日程。清军在乌兰布通击败噶尔丹蒙古军后,清廷一改历史上封建王朝修筑长城戍守之成规,主动出击,变军事防御为军事进攻。规模较大的右卫八旗驻防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设置的。
二、右卫将军与右卫驻防旗兵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康熙皇帝开始着手右卫驻防的具体事宜,他先后派大员往勘右卫城(今山西右玉县右卫镇)和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旧城)一带的地形风貌,几经周折,最后决定在右卫城设置八旗驻防。据《清实录》记载:“先是,上以西北有警,命户部尚书马齐,兵部尚书索诺加,往勘归化城驻兵之地。至是马齐等疏言:‘臣等查勘,右卫与归化城相近,应移右卫人民出城外,令住郭内,城中盖造房屋,可以驻兵。杀虎口外迤北五十里,东西五十里内,所有熟荒地亩,近者给兵,远者给大臣官员。归化城小,地荒田卤,难以耕种;归化城西南三十余里外,有浑津村,村南十里外,有浑津巴尔哈孙旧城基址,城北有大土尔根河,周围三里余,宜展此基址,一面三里,筑土为城,造房驻扎官兵;城之四周所有田地,可取以给官兵耕种。’命议政王大臣等议。寻议覆:‘归化城之浑津巴尔哈孙无城,右卫见有城,且近归化城,大宜驻兵;其往驻时,应拨每佐领护军三名,骁骑校三名,汉军火器营兵一千驻扎,统以将军一员;每翼护军统领各一员,满洲副都统各一员,汉军副都统各一员;每旗协领各一员,佐领各七员,防御各七员,骁骑校各七员;其协领以实授参领遣往,护军每旗以实授护军参领各四员,护军校各七员;汉军一千名,以每翼协领各一员,每旗佐领各二员,防御各二员,骁骑校各二员,令其约束;每佐领,拨拨什库六名;护军、拨什库、骁骑仍照京城例,给以钱粮,驻兵既发之后,按缺补足;其喀尔喀、阿尔萨、阑戴青等人丁,三丁合披一甲,可得甲九百六十五名,以五十名为一佐领,编成十九佐领;蒿齐忒郡王达尔玛吉里迪旗下人丁,亦以三丁合披一甲,可得甲一百五十四名,编为三佐领,所余人丁作为附丁,选择材干善于约束之台吉头目,授以佐领、骁骑校,附归化城土默特两旗,在归化城四周游牧;再发绿旗马兵一千,步军二千驻扎,设总兵官一员,标下立为五营,如有事当行,此新设总兵官及宣大两镇标下官兵,俱听将军调遣;将军以下大小官员口粮及马之草料,一概停给,以口外五十里以内荒地给之,自力开垦;右卫城内所有民房俱给价购买,安插官兵。’上曰:‘城内居民,若令移于郭外,必致困苦,可勿令迁移,照常居住;若造官兵房屋,城内难容,即于城外建造;此满兵有事即行,不必授田,大臣官员,宜给予口粮,马给草料,务使势力有余;至于绿旗官兵遇调用,则宣大绿旗兵在近调发甚便,停其添设,其缺以满洲官兵增驻;所发护军之缺,应即补充;骁骑火器营兵之缺,应行停止;官兵住房,宜拨往驻大臣官员监修。’著再议。寻议覆:‘增设绿旗官兵应停止,每佐领增发护军三名、骁骑校一名,每佐领兵共十名;其护军,每旗发实授护军参领七员,以一员为夸兰大,设护军校十四员以领之;驻兵既拨之后,其护军之缺补足,骁骑火器营兵之缺,不必补足;城内居民不必迁移,官兵住房,拨工部堂官一员、驻防大臣内每翼一员及每旗护军参领等一员监造;官员口粮,照例给发,马匹草料,夏秋停给,令其牧放,其口粮草料,一半折给,一半本色;将大同府应征地丁银,改征本色,以给官兵。’得旨:‘每佐领减去护军一名、校骑一名,余如议。’随授都统希福为建威将军,噶尔玛为左翼护军统领,四格为右翼护军统领,方额为左翼副都统,马锡为右翼副都统,张素义为左翼汉军副都统,吴兴祚为右翼汉军副都统,令驻右卫。[2]右卫将军的全称为:“钦命镇守朔平等处地方、辖满洲蒙古汉军八旗官兵,建威将军”。随着右卫八旗营房的迅速建成,右卫将军希福亲率满蒙汉八旗兵进驻了右卫城(满洲兵多为京旗人)。现右卫城一带的北草场、南草场、马营河、红旗口等既是当年八旗兵的居所遗存。杀虎口外的和林格尔境内有右卫八旗兵广袤的八旗牧场。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九月,清廷又“选来堪披甲蒙古三千六十五人,……令驻右卫。”[3]至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右卫将军辖有八旗属官406人,其中左右翼护军统领2员,左右翼副都统4员,左右翼协领10员,护军参领56员,佐领72员,防御72员,骁骑校72员,护军校112员,将军笔帖式4员,护军统领笔帖式2员;辖有满蒙汉八旗兵4903人,其中护军2299人,马兵2604人。总计辖有旗官和旗兵5309人。[4]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十月,费扬古身兼右卫将军和归化城将军两职,这显然是为防御和进击噶尔丹的战事所设。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春,清军分东、中、西三路进击噶尔丹。费扬古亲率以右卫八旗兵为核心的西路军北征,五月,在昭莫多地方与噶尔丹军展开血战,致使噶尔丹的精锐部队损失贻尽,噶尔丹仅率数十骑逃走,右卫八旗兵因此而威名远扬。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昭莫多之战”。同年九月,康熙皇帝出巡归化城和鄂尔多斯蒙古部。十二月初七日,康熙帝在回京途中经过杀虎口,初八日,抵右卫城。在此,康熙帝巡阅了右卫八旗兵,布署了对噶尔丹残部的军务。康熙三十七年(1698),驻防右卫的旗兵大多撤回京城,留下无人居住的营房甚多,为解决京城旗人滋息甚繁无兵额可补之窘状,康熙五十年(1710年)在右卫添设了八旗马兵1000人,雍正九年(1731)又添设八旗马兵500人。[5]后随着西北八旗防务体系和准噶尔汗国军情的变化,清廷深知右卫驻防城太靠南,不利于进击准噶尔蒙古部和控制内蒙古西部蒙古诸部,驻防重心需北移,故在乾隆二年(1737年),右卫将军迁驻于绥远城(今呼和浩特市新城)。随之,右卫八旗驻防降格为副都统所辖,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又降为城守尉所辖,隶于绥远城将军。
清代的右卫将军始设于康熙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止于乾隆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历时45年,共有8位将军就任,现分述如下:
1.希福:康熙三十一年(1692)十二月二十八,都统希福率八旗兵首驻右卫,为右卫将军,并授建威将军。康熙三十四年六月初四被革职。期间,康熙三十二年五月初七,清廷授三等伯、内大臣费扬古为安北将军,驻归化城,管理归化城事务。康熙三十三年七月初七,费扬古西征凯旋后,清廷授其将军印,并兼任右卫大臣。
2.费扬古:康熙三十四年(1695)十月初四,清廷授费扬古为右卫将军,并兼归化城将军事务;十一月三十,又授为抚远大将军。康熙三十五年(1696),因出征蒙古噶尔丹,被免去右卫将军职务。
3.费扬固:康熙三十五年(1696)十二月初九,清廷提任护军统领费扬固(宗室旗人)为右卫将军。康熙五十一年(1712)正月二十九,又封为辅国公。康熙五十七年正月二十六,因病被免职。
4.颜寿:康熙五十七年(1718)三月十七,清廷提任归化城副都统颜寿(觉罗旗人)为右卫将军。雍正二年(1724)六月十七,降为左翼副都统。
5.吴礼布:雍正二年六月十七,清廷提任右卫右翼副都统吴礼布为右卫将军。雍正四年(1726)二月二十八,调任为八旗蒙古正黄旗都统。
6.申穆德:雍正四年二月二十八,清廷调任八旗蒙古正黄旗都统申穆德(宗室旗人)为右卫将军。雍正十三年(1735)十一月被免职。
7.岱林布: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清廷调任八旗汉军镶红旗都统岱林布为右卫将军。乾隆元年(1736)十二月二十八,改任为江宁将军。
8.王常:乾隆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清廷调任参赞大臣王常为右卫将军。乾隆二年(1737)三月二十二,清廷令王常率部分右卫八旗官兵调迁新筑之绥远城。
三、绥远驻防城中的原右卫旗兵
雍正末年,清朝与漠西准噶尔部的战争几经较量均已无力再战,只得议和,双方偃旗息鼓、撤军回寨,漠北一时出现了和平局面。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二月清廷决计在归化城旁建一新城——绥远城,以安排从漠北撤回的军士。对此《清实录》有详细记载:“总理事务王大臣奏言:大兵既撤,若喀尔喀蒙古等必需内兵防护,请酌留东三省兵五千名,驻扎鄂尔昆。现今鄂尔昆贮米甚多,可支五千人数年之食,其察罕瘦尔所贮粮三万余石,亦应运赴鄂尔昆。又归化城,路当通衢,地广土肥,驻兵可保护扎萨克蒙古等,调用亦便。请于右卫兵四千内,酌拨三千,并军营所撤家选兵[6]二千,热河鸟枪兵一千,并令携家驻归化城。若喀尔喀等自能防守,鄂尔昆不必留驻内兵,则归化城请再酌增兵四千为一万人,令其留戍。设将军一员总理,副都统二员协理,所留右卫兵一千名,以副都统一员领之,仍隶归化城将军管辖。并请特命大臣一人驰往,会右卫将军岱琳卜,归化城都统丹津、根敦、尚书通智等,相视形势,其戍兵如何分驻,及筑城垦田以足兵食等事,详悉确议具奏。……从之。”[7]也就是说,清廷准备裁右卫将军,并在归化城旁建一新城,新设将军一人统辖兵丁。
当筑城屯兵之举正处于筹划之时,官居“稽察归化城军需工料掌印给事中”的永泰为长远计,于乾隆元年(1736年)四月上奏道:“归化旧城,修整完固,于城东门外,紧接旧城,筑一新城;新旧两城,搭盖营房,连为犄角,声势相援,便于呼应。右卫驻防兵丁,不宜迁移,镇守仍照旧制,庶于地方有益,归化城一带地亩,不便改为民种升科。”乾隆认为永泰言之有理,遂改初衷,于是下令:“筑城开垦事件,交通智总管办理,俟城工告竣之时,先派家选兵二千名,热河兵一千名前往驻防。其家选兵照八旗另记档案人例,另记档案,将来补授骁骑校等微职,不可用至大员。右卫兵丁,暂行停止迁移,仍著在本处驻防。归化城周围田地,悉行开垦,俟积谷充裕之时,于京城八旗闲散满洲内,将情愿者,挑派三千名,以为新城驻防兵丁,其钱粮家口米石及拴养马匹,俱著照热河兵、家选兵例。”[8]这样先前调迁右卫旗兵的动议改由京师满洲兵驻防绥远城,而热河兵及家选兵3000人依议未变。
七月,清廷将在漠北军营已征战五、六年的京城家选兵2000人,因作战军功均提高身份,由以前的八旗家仆分立另户,“归入旗分”,成为有一定待遇的汉军旗人。十二月,乾隆谕令速建绥远城,并告知筑城官员:驻防兵丁“于明春即当遣往”。[9]
乾隆二年(1737年)三月,清廷又决定在绥远城停增新设将军,只需将右卫将军迁此即可,同时暂停派遣京师旗兵。《清实录》云:“总理事务王大臣议奏:归化城盖造新城,去右卫仅二百里,无庸添设将军,请将右卫将军移驻新城,止添副都统二员,其右卫之副都统二员仍留原处,亦归并将军管辖。所有家选兵二千名,热河兵一千名,蓍该处照原议办理,俟房屋工竣日,先往驻扎。其管兵官员,应令将军王常等,会同八旗大臣,拣选京城应升官员,请旨补放。至京城应派官兵三千名,遵旨暂停,俟归化城附近地亩开垦足数,呈报到日再议。从之。”[10]
在六月之前,绥远城营房已完工,按既定方针,从漠北而来的已成另户汉军的原2000家选兵及热河汉军1000人率先进驻绥远城。《清高宗实录》对这3000旗兵的驻防具体时间无记载,但在六月丁卯条上云:“总理事务王大臣等奏:热河地方,甚为紧要,所居满洲兵现有八百名,其从前一千操演兵(即鸟枪兵)已遣往归化城驻扎……”。这说明3000旗兵当在乾隆二年六月前的春季驻防无疑,也正符合乾隆“明春即当遣往”的谕令。
八月,从右卫将军任上调迁而来的绥远城建威将军王昌,根据驻防伊始,需立即筹办增添兵丁,选派官佐,制定仪卫,奏定钱粮等事宜,上奏了九条急需之应议事件。据《清实录》记载:“又议复归化城将军王昌奏:新驻兵丁,应议事件:原附右卫蒙古裁汰余兵五百名,请编为五个佐领,移驻新城仍照原议支给官弁俸饷。新城驻扎兵丁,须得熟谙之员经理,请将右卫官员,酌量送部引见调补。新城将军以下,笔帖式以上,应得米石马匹,照右卫例支给。新城应设铁匠箭匠,照右卫例挑取,给予银粮。将军仪卫,照提督例;副都统仪卫,照总兵例,由巡抚处领取;执事人应得银两,照右卫例,在同知库内支取。新城应用旗……,照例由部领取。兵丁马匹,除现有分给外,尚有不敷,由扎萨克办给。每佐领设领催四名,每名给钱粮三两。请设左右两司,给予关防,协御给予图记,均应如所请办理。惟称将右卫随印前锋,随往新城,伊等转有迁徙之劳,应令于新驻兵内挑取,添给钱粮一两,其原存右卫者,酌量挑取,随副都统驻扎,其余陆续裁减。又军器一项,自应豫为制办,请每兵四名,给账房一架,器械计人分给,共给鸟枪六百杆,选择兵丁,令其练习。火药等项由部支领。又本练兵等事,应用炮药,由地方官领取。”乾隆认为王昌筹划合理,挥笔批示:“从之”。[11]自此在原3000旗兵的基础上,又从右卫蒙古八旗中调来五个佐领的500旗兵,绥远城共有旗兵3500人,但佐领以上大员,大多从京旗及右卫满洲内调补。
乾隆六年(1741年)三月,新任将军补熙看到缓远城兵多官少,不敷统率,应从右卫移驻少许下级官佐,故奏准“将右卫正红、镶白、镶红、正蓝、镶蓝五满洲旗分内,每旗拨佐领、防御、骁骑校各一,董率兵丁。[12]”共计15名下级官佐移驻绥远城。
乾隆十二年(1747年)已是汉军旗人的原京师家选兵2000人在绥远城遭到裁汰,出旗编入绿旗营。同时,酝酿已久的京旗满洲兵1200人,大规模地首次进驻绥远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驻守绥远城近30年的热河汉军此时虽然兵丁数已翻一番(2117人),成为驻绥远城主力,但也只能步京师家选兵之后尘,清廷谕令其全部出旗入绿旗营。绥远城只剩旗兵1300人。
乾隆三十年(1765年)五月,将军蕴著又觉满蒙旗兵兵力太少,不敷应用,奏请增兵为2000人。奏折云:“绥远城官五十四员,兵一千三百余名。右卫官四十八员,兵一千五百余名。二处官兵多寡不同,请量其敷用均齐。将绥远城满洲作为佐领十六,蒙古作为佐领四,共二十佐领。……又绥远城、右卫二处,每兵百名作为一佐领,每佐领下除匠役二名外,领催、前锋、马甲共七十五,养育兵、步甲共二十五。绥远城应兵额二千,现一千三百。不敷满兵七百,于由京派来驻防兵内补;不敷蒙古兵一百,于右卫蒙古余额兵内补。乾隆批示:“从之。”[13]这样,又有100名八旗蒙古兵,从右卫调迁绥远城驻防。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清廷又决定在绥远城增设兵额。《清朝文献通考》云:“增马步兵七百名。”而《绥远城驻防志》记载较详:“将右卫兵丁内,移驻绥远城马甲五百名,步甲一百五十,养育兵五十名,添入八旗满洲、蒙古各佐领下当差。合本城兵二千名,现在实存兵二千七百名。内:领催、前锋、马兵二千名,步兵四百名,养育兵三百名。”这2700名旗兵中,甲兵为2000人,但多数为京师满洲旗人所有,今绥远城满族语言多操京腔,盖源于此。从右卫而来的700满蒙旗兵,满洲旗人当为绝大多数。遍检典籍,右卫满洲兵大规模地驻防绥远城,终清一代只此一次。需要说明:从1768年起,绥远城旗兵日后再无相互调防之举,只有随着人口的滋生,旗兵总数亦增添而已。
以上统计,有清一代,清廷在1737年、1741年、1765年、1768年,共四批次迁调右卫满蒙旗兵1315人驻防绥远城。
四、余论
1.清朝是以满族为主体而建立的一个封建专制王朝。它统治幅员辽阔的中国长达268年之久。它的盛时疆域,东北至外兴安岭及库页岛,北达恰克图,西北到巴尔喀什湖和葱岭,南抵南海诸岛,东到台湾。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着满、汉、蒙、回、藏等50多个民族。他们在这个统一的国家里,进行着政治、经济、文化的交往,从而推动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的进步。清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所以得到巩固和发展,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各民族间的共同利益、共同命运、共同追求,始终像一条纽带把他们紧紧联结在一起。这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以发展和巩固的根本条件,也是有清一代建立巩固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基础。清初的满族是一个新兴的民族,它以崭新的面貌和旺盛的活力登上了中国历史舞台,当它加入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后,以其勃勃生气,肩负起了历史使命。有清一代,满族人民与我国各族人民一道,为要求统一、坚持团结、反对分裂、防御外敌的共同利益而斗争,为推动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写下了不少光辉灿烂的篇章。具体讲,右卫和绥远城的设置,在巩固和保卫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屏藩朔漠,有着不可估量的历史作用。驻防旗兵们披坚执锐,露宿风餐,汗马血战,百死一生,为稳定北部边疆乃至中华民族的疆域立下了殊勋。
2.清代的八旗兵,除当兵食饷外,不从事其它生产活动,日常生活用品全靠外界供应和自行购买,故八旗驻防城建立伊始就成为商贾云集的中心。如右卫驻防城设置后,大量晋商云集于此,从事南北物资贸易,以供旗兵的日常生活,从而给杀虎口一带的社会经济带来了空前的繁荣。右卫将军迁驻绥远城后,大批晋商继续随之与旗人贸易,当时绥远城东、西、南、北四条大街两旁充满了晋商的林立店铺,他们或贸易,或佣工,各种商店酒馆,工匠铺等应运而生。据《清实录》记载:因筹建绥远驻防城,“数年以来,归化城商人糊口裕如,家赀殷富,全赖军营贸易生理。”[14]这时的归化域已成为人烟稠密的商业中心。绥远城设置后,归化城的经济贸易日趋发展。据文献记载:“归化仅弹丸之地,戏楼酒肆大小数十百区,镇日间燔炙煎熬,管弦呕哑,选声择味,列坐喧呼。问之则曰:某店肆新开燕贺请客也;又问之则曰:某店肆算帐赢余请客也;再问则曰:某店肆歇业亏本抵债请客也。循环终岁,络绎不休。而开设戏楼酒肆之家亦复彼此效尤,恣情挥霍,不数月而转易他姓矣。”[15]归化、绥远两城的商业繁茂,由此可见一斑,这是其经济繁荣景象的真实写照。
3.随着清朝对全国的统一,长城内外的蒙汉居住区连为一体,这就为蒙汉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和长城内外的人口流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清廷利用国家政权力量,随时调整其对蒙汉地区的统治政策,实行“移民实边”或“借地养民”等政策提供了可能。“走西口”的移民潮就是在这种前提下产生的。绥远城的设置,数千八旗兵连同上万眷属屯居一处,生活用品和粮食的供给自是首要大事。这就极大地刺激了山西流民的经商和垦荒心愿。他们不顾朝廷禁令,三五成群,跟踵而至。清朝中后期,随着蒙古地区驰禁放荒,从而为内地大批破产流亡农民出塞谋生铺平了道路,由于天灾人祸,山西的流民不畏艰辛,成群结队,扶老携幼,风餐露宿地“走西口(出杀虎口),去归化”,蜂涌进入内蒙古中西部各地觅食求生和经商谋利。先为春去秋归的“雁行”客户,后由于聚族日繁而定居长住,并逐渐成为当地人口的大多数。久之,使昔日广袤无垠的游牧区,逐渐变为蒙汉杂居、耕牧兼营的半农半牧区。蒙古地区农业的发展,不仅促进了蒙古畜牧业的发展,也促进了蒙汉人民间的互助合作。蒙古牧民向汉族农民学会了耕种耘耨的农业生产技能,汉族农民向蒙古牧民学会了经营畜牧业的经验与技术。总之,移民的到来和蒙地的开垦,改变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随着右卫驻防城的设置,许多满族的习俗从北京、东北地区带到了这里。随着绥远城的设置,满族和山西汉族的风俗又带到了呼和浩特地区。满蒙汉回四个民族的生活习俗在呼和浩特地区相互影响和交融,极大地丰富了这一地区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例如,旗人初来绥远城时,只会满语,不谙汉语,但由于长期处于汉族人民的包围之中,日常交往离不开汉语,至清朝末年,旗人已多不会满语,多改说汉语;同样,由于绥远城内的山西商人多年与满族交往,也多会说京腔北京话,他们自称这种京腔汉语为“满洲话”,至今这种京腔北京话仍在他们的后代中对外说用。此外,满语传入呼和浩特地区,极大地丰富了当地汉语的语汇,至今呼和浩特地区的汉语中,保留有许多满语词汇和大量的蒙古语词汇。又如:在今呼和浩特地区汉族的婚礼中,仍保留有男方娶亲时须给女方家留下“离娘肉”的习俗,而“离娘肉”正是满族古老的婚俗之一,因在长期的满汉文化交往中,这一习俗已被汉族所吸取。此外,满族习俗对土默特蒙古人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据《土默特旗志》记载:“蒙人生子有尽剪发者,留囟门发一摄者,名曰马发。十二岁到奶奶庙以骑驴还愿,或杂以草。后留发辫曰十二和尚。……女十五以上戴笄,即满洲大簪也。”[16]而这些土默特男子和女子的头饰,正是清代满族头饰的一部分。再如:绥远城旗人家遇丧事穿孝服时,从北京、东北来的旗人后代鞋上均不蒙白布,而右卫旗人后代则蒙之,由此便可知此户旗人的由来,这是旗人受山西汉族文化影响的一个范例。此外,在饮食方面,满蒙汉回四个民族的相互影响和交融更是数不胜数。
注释:
[1]《东华录》卷二十,康熙五十六年十月已亥。
[2]《清圣祖实录》卷157,康熙三十一年十二月壬寅。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本。
[3]《清圣祖实录》卷160,康熙三十二年九月庚午。又据《朔平府志》记载,该兵为出生于喀喇沁蒙古的旗兵,雍正三年(1725)又被调往喀尔喀蒙古察罕叟儿地方驻防。
[4]《朔平府志》卷八《武备志》。
[5]同上。
[6]家选兵,清代满洲等旗人之家仆(多为汉人)因跟主人出征而获兵籍者的称谓。此前家仆因其身份低下,无独立户籍,只能依附于主人户下,故亦称“户下”或“家下”人。但如因军功等原因,可偿还主人身价后,从主人户下分离出来另立户档,名曰“开户”或“另户”,但多入汉军旗籍并被另记档案。
[7]《清高宗录》卷九,雍正十三年十二月丙戍。
[8]《清高宗实录》卷61,乾隆元年四月甲戌。
[9]《清高宗实录》卷32,乾隆元年十二月庚午。
[10]《清高宗实录》卷39,乾隆二年三月庚戊。
[11]《清高宗实录》卷48,乾隆二年八月丙寅。
[12]《清高宗实录》卷138,乾隆六年三月戊寅。
[13]《清高宗实录》卷736,乾隆三十年五月丁亥。
[14]《清高宗实录》卷412,乾隆十七年四月辛卯。
[15]《古丰识略》卷21。
[16]高赓思:《土默特旗志》卷8,光绪三十四年木刻本。(作者:内蒙古社会科学院)
- 年鉴刊物上一篇:(史海钩沉)古城掘疑——吕布出生地暨九原郡考
- 年鉴刊物下一篇:(史海钩沉)强盗政治与名士风流——两晋历史三题
- 声明: 转载请注明来源于《内蒙古区情网》官方网站














 当前位置:
当前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