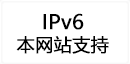第五期
- 【导读】本期导读
- 【特载】2014年全国方志期刊工作座谈会纪要
- 【志鉴论坛】地方志要重视对地域文化的收集整理和开发利用
- 【志鉴论坛】关于地方志人物简介的思考与实践
- 【志鉴论坛】说说志书竖写的自然段划分问题
- 【志鉴论坛】运用理论指导设置篇目
- 【史海钩沉】契丹后裔今何在
- 【史海钩沉】打响蒙古族抗日第一枪的民族英雄陶格陶胡
- 【史海钩沉】通辽伉俪——记革命伴侣吕明仁与丁修
- 【史海钩沉】给周总理写信的“草莽之人”
- 【方志大观】内蒙古方志纵横
- 【方志大观】修志问道 尽责圆梦
- 【申遗履痕】让草原文化遗产之光在世界闪耀——元上都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历程回顾
- 【地名文化】呼和浩特地区村落名称掌故(下)
- 【地名文化】三个地名考——蜈蚣坝、宝格达山、西口三地名的由来
- 【盟市园地】旅蒙商、龙票、海拉尔商业“八大家”考略
- 【盟市园地】清末民初的扎兰屯
- 【工作指南】现代科技与思想政治工作现代化
- 【大事记】内蒙古大事记(2014年8月21日~10月20日)
- 【珍珠滩】大头喇嘛
- 【珍珠滩】乌梁素海(外一首)
- 【书画摄影】全区地方志系统书画摄影赛摄影获奖作品
- 【书画摄影】全区地方志系统书画摄影赛书法获奖作品
- 《呼伦贝尔市志(稿)(1990~2005)》评审会召开
- 乌海市召开电视片《方志内蒙古(乌海集)》拍摄协调座谈会
- 《内蒙古自治区志·统计志(1998--2013)》(稿)评审会召开
- 全区地方志系统信息网站建设基本完成
- 2014新方志论坛在成都举办
- 【志鉴动态】全区方志馆建设进展顺利
- 自治区地方志办公室开展盟市网站培训工作
- 【珍珠滩】大头喇嘛
- 发布时间:2015-03-04
- 来源:本站原创
一
五更天,丹宾嘉禅醒了。大头喇嘛城响起有节奏的敲击声,那是铜锣的响声。其实,不用敲击这个时候他也会醒来。自打率众来到马鬃山,就从没有睡过安稳觉。哲布尊丹巴活佛的人如果偷袭,现在是最好的时机。他习惯地把硕大的脑袋侧向石头窗口,仔细听了一阵。不过,除了信徒们的酣睡声,只感受到一股低沉、有力的气流,他明白这是风吹过戈壁的声音。现在是十月初的光景,正值马鬃山麓草黄马肥的季节,天气开始变冷,很快就要下第一场雪了。梭梭林透出阵阵腥甜的气味,令人联想到陈酿驼奶酒的味道。
丹宾嘉禅围坐在羊皮被褥里,从石头窗口眺望着棉絮状云间闪露的星斗,孤独的感觉不由涌上心头:在这浩渺的苍穹间,人是多么微不足道呵。
那还是民国8年冬天的事了,数百名忠实的信徒追随自己,闯进了马鬃山。他们如同开河的冰凌,吓得伊克高勒的汉人东躲西藏,唯恐殃及自身。到了这会儿,丹宾嘉禅又想起了马鬃山的地头蛇张玉麟张团总,他是个城府极深、很有教养的山西人。面对饥饿的哀兵,张团总如同上了岁数的庄户人,圪蹴在通往安西路口的土墩上,吸着水烟,迎风眯缝着双眼,望着北边山峦间升起的滚滚尘土,眼角牵出了很深很长的鱼尾纹,一直延伸到了嘴角,心事重重地看了许久,在乡丁们的护卫下,坐着骡轿离开了老营。临走,撂下一句话:“马鬃毛里藏不住虱子,马鬃山里容不下强盗,他们呆不长。”
确如张团总所言,大头喇嘛的信徒该散伙了。
其实在一年前他就明白了,自己的使命已经结束。自己在这里苦苦挣扎,和那个大战风车的外国傻子又有啥区别呢?不禁想起承化寺主持的教谕:“一事了结,其收场就临近,开场已成收尾。”
丹宾嘉禅清楚自己的心态老了。虽说还不到40岁,每天半夜都会惊醒,一切平安,却再难以入睡。自从到了马鬃山,哲布尊丹巴的刺客如同戈壁黑苍蝇,幽灵似的时时纠缠着他。已经多少次有惊有险或者有惊无险了?仰望着窗口的云团、星斗,他在心理数着,这几乎是每天黎明时分的必备功课了,可是每次数的数都有出入,不是少了就是多了,他便暗自笑话自己:瞧瞧,连这几个数都算不清楚,哪里还有一点神童兼活佛的影子呢?不过只要抚摸一下新旧伤疤,都能回忆起受伤时的情景,每一处伤几乎都要了他的命。也就是说,每回都是福大命大造化大,是死里逃生啊,难怪信徒们对他是更加崇拜了。
他就这样坐着,任思绪信马由缰。
丹宾嘉禅少年时代留学俄国,熟知蒙藏汉俄4种语言文字,曾专赴俄军驻地,潜心学习新式练兵之道,想弄清楚中国为什么丧权辱国。回国后又游历了新疆、内蒙古和北京等地,不禁暗自倒吸一口凉气:大清朝气数尽了!心灰意冷之下,骑着那峰著名的白骆驼,遍游了外蒙古各旗。有人询问姓名,总是自称穷喇嘛,也有人叫他白驼喇嘛。因为丹宾嘉禅头颅硕大,引人注目,大头喇嘛的名声便在外蒙古广为流传。后来哲布尊丹巴大活佛邀请他去库伦,商讨蒙古复兴大业,几番讨论,丹宾嘉禅终于明白:道不同不相谋,两人不是一条道上的朝圣者,要参拜的可不是同一座圣山啊。
“蒙古要想复兴,必须恢复成吉思汗基业,不受大清管束。”
大活佛绕了半天弯子,这才说道实质。
“不!”
丹宾嘉禅摇了摇头,“中国自古合则强大,分则削弱。自大元灭亡,满蒙汉藏回五族共存,断无蒙古独立之说。即便建立所谓的国家,也不过是他人傀儡。请大活佛不要忘记,我们的北边可有一只贪得无厌的大狗熊啊!”
两位活佛便冷了场,无话可讲了,于是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了。丹宾的信徒越来越多,哲布尊丹巴大活佛终于感到了威胁,他可不喜欢有人挑战自己的权势,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于是杀手陪伴大头喇嘛的岁月开始了。
黎明前的黑暗里,丹宾嘉禅忽而觉得悲哀,忽而觉得焦灼不安,体内的火在燃烧,感到异常口渴,就想到应该喝点什么。他从铺着羊皮被褥的床榻起身,懒得点燃羊油灯,在这间狭小的石头房里摸了一遍,从桌下摸出一只坛子,用铜勺舀了一点驼奶酒,慢慢润进嗓子。就在去年这个时候,他还能一口气喝下半口袋驼奶酒,可是自从听说宿敌被囚的消息后,似乎一个晚上的工夫,就失去了豪饮水平。喝急了就呛得肺子疼,必须在嘴里暖暖才敢咽下去,不然就如同三九天掉进了冰窟窿,寒气浸入骨髓不说,连心肺都冷得疼痛。
就这样没滋没味地小口喝着酒,突然间活佛有些慌神,他想起还有件事没办,就对着厨房喊道:“黄胡子!黄胡子!”黄胡子不仅骑射超群,还做得一手好饭食,由他经管活佛的饮食,信徒们极为放心。厨房就在隔壁。在残山戈壁的黎明时分,丹宾喇嘛的喊声听起来尤为苍凉,又特别惊魂,喊过几声,活佛才想起来,为了让刺客得手,两天前黄胡子元旦和独辫已被打发到安西城了。
明白这事别人代替不了,丹宾嘉禅心底反倒踏实了许多,把棉袍、皮裤、靴子穿好,又套上一件羊皮袄,仔细扎好腰带,拿起左轮手枪,端详一阵,又放在床上。这还是俄国朋友的礼品,平日枪不离身,信徒们都说,活佛拿枪的时间比念佛经的时间还要长,既然打算去送死,要枪干啥呢?他笑着摇摇头,便出了石头房子。
二
大头喇嘛城堡位于马鬃山北麓的丘陵地带,北部是著名的公婆泉,又称滚坡泉。丹宾嘉禅率众进入额济纳扎萨克旗,在这里凿山砌石筑成坚城,用石头和泥巴砌成的灰墙高达三丈。城池周围数里,城东蒙古包纵横,宛如街市;城西营房操场,星罗棋布。百里之内一览无余,俨然是军事重镇。
活佛的座骑白骆驼卧瞭在望塔下静静地反刍,唯独它可以到处闲逛,不受拘束。在黎明前的夜色里,白骆驼隐约可见。只要不去厮杀,丹宾嘉禅总是骑着它。路过契丹吉宁等三人的毡包,听见里面酣声如雷,便暗自好笑:配当刺客吗?本活佛就在门外,等着你们呢。唉,凡人就是凡人!看到那团隐约的白色,丹宾喇嘛就低低呼唤座骑。
白骆驼应着呼唤,无声无息地踱了过来。戈壁的星光,勾勒出白驼庞大、优雅的轮廓。牧人们都说,白骆驼有神呢,千万峰骆驼里,只有它最俊美,也最通人性,要不咋就成活佛的座骑呢?白骆驼慢悠悠地踱过来,谦恭地卧下身子,抬起聪颖的双眼,亲昵地嗅着主人,丹宾嘉禅就跨上了双峰直立的驼背。冷清的北风从公婆泉那边吹来,带着一股股芦苇陈腐的腥气。喇嘛坐稳了高大的身躯,抖动缰绳,白骆驼就嘶鸣一声,先支起后腿,弓圆了身子,前腿一站,不用主人驱赶,向东院门走去。
白骆驼的步伐很大,也很平缓,载着身穿厚重羊皮袍的丹宾喇嘛走出东寨门。丹宾歪身陷在驼峰间,眼睛都懒得睁开,似乎又回到了儿时的岁月,自己被父亲扶上那神奇的摇篮,那雕花的马鞍,母亲那双还散发着羊乳香味的手,轻轻抚摸着他的后背。哦,母亲,当你的灵魂升上天国之后,用散发着乳香歌声轻轻抚摸我后背的女人,就是那蒙古草原最美丽、歌喉最甜美的斯琴姑娘啊!
斯琴,你在哪里?
丹宾的眼睛潮湿了。
等他慢慢睁开眼睛,这才发现已到了火烧井。数条交叉的商路汇集这里,这里离公婆泉城很远了,在马鬃山和北山黒黝黝的影子下,辽阔的戈壁滩边缘捧出一掬朦胧的弧光。黎明前的夜色又黑又稠,那缕迷蒙的弧光与颤动的星光交融着、闪烁着,似乎随时会融进夜幕,却又的确横卧在远处。丹宾喇嘛知道,那是伊克高勒——大河的最后集水地,这是大头喇嘛今天要去的地方。
斯琴——
丹宾嘉禅难受地抬起硕大的头,长长吐出一口气。
北风擦过草梢和驼峰,丹宾喇嘛不觉坐直身子。无数次的回想、无数次的愤懑,已使他失去了最初的狂暴,心还在淌血,已不再形于声色,特别是哲布尊丹巴的失势,让他心绪茫然,如同一个古代的侠客,拔剑四顾,却寻找不到敌人,这是何等的悲凉。
三
作为哲布尊丹巴有力的敌手,丹宾喇嘛已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了,由于和杀手交手的次数多了,竟想不起到底有多少回了,唯独与一名女杀手的相逢,教他难以忘却。到马鬃山的次年春天,公婆泉来了一户牧人,那老者长着一部雪白的长髯,他的身旁是一个妙龄少女,怯怯的黑眼睛打量着独辫。察苏台委实也过于吓人,骆驼般高大的身躯,刮得红柳枝乱舞。走近简陋的蒙古包,咚咚的脚步一踩一个坑,吓得猎犬蹿进了红柳林。
“你们从哪来?”
他是大头喇嘛的贴身卫士,不放过任何可疑来人。
“我们父女是丹宾大活佛虔诚的信徒,从科布多追随佛爷的足迹而来。”老者诚恳的回答和妙龄少女怯怯的黑眼睛,终于消除了他的疑虑。他们在公婆泉往了下来,老者带着黑眼睛的女儿时常到堡寨里听活佛的诵经布道。有一天丹宾嘎拉僧终于注意了这父女俩,是听到老人慈爱地呼唤“斯琴”的声音。喇嘛叫住了父女二人。
“你是斯琴?”
他凝视着她怯怯的黑眼睛,心头一阵悸动。
“回佛爷的话,我叫斯琴塔娜。”
“哦,斯琴塔娜……”
丹宾嘉禅若有所思又看了一眼少女,慢慢踱回了他的居室。
当天晚上,独辫抱羊羔似地把黑眼睛少女夹到了活佛面前,“大活佛,我把她带来了。”
“你这是干啥?”活佛有些愠怒。
“她也叫斯琴。”察苏台依旧是一副面无表情的模样。
丹宾嘉禅咬紧下腭,盯着独辫,好半天才挥挥手,“你去吧。”
他在石地上来回走了几步,对缩在屋子一角打哆嗦的少女说:“你别怕,我叫人送你回家。”
“为什么,”少女轻声问,她的声音很好听,“佛爷是看不上我吗?”
大头喇嘛转过身来,很有耐心地告诉她原委,“虽说哲布尊丹巴骂我是强盗,方圆几百里也没人说我好,但我不会欺负一个无助的人。”
少女的眼睛里充盈了泪花,“佛爷,您允许我陪您说说话吗?”
丹宾喇嘛禁不住笑了,“好嘛,那就陪本佛爷说说话吧。”
那一夜,在摇曳的羊油灯下,大头喇嘛与黑眼睛少女谈了很多,从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尖塔到北京紫禁城的佚事传说,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月夜说道金色圣山的佛光,从马鬃山凛冽的北风回味家乡科布多奶牛浓郁的乳香,两人兴致勃勃,侃侃而谈,喝光了三坛子奶酒,可是谁也没醉。
天快亮时,黑眼睛少女突然跪下,泪珠扑簌簌滚出眼眶,“佛爷,我和阿爸是来杀你的。你是好人,我不能干,请佛爷赐我死吧。”说着,她从衣襟里掏出一把小巧的手枪,双手捧着举过头顶。
大头喇嘛缓缓放下银碗,不易觉察地摇摇头,轻轻长叹一声。
“哐啷!”
独辫和元旦破门而入,察苏台一把夺过手枪,扯住她的领口,枪口对准少女额头,按下保险就要搂火。
“慢着!”
大头喇嘛厉声喝止。
独辫一改平日不动声色的神情,急切地大喊:“佛爷,她可是要杀你的呀。”“啍!”大头喇嘛从鼻子里喷出两股不满的气息,“她要想杀我早就动手了,哪有你们救我的机会。”
“嗐!”
察苏台推开少女,大步冲出房门,接着听见他洪钟似的吼声:“开大门,跟我去抓刺客!”
纷乱的马蹄驰出营寨,就听见奔向北边的公婆泉。
一个时辰后,庭院里传来马队的声音,独辫察苏台大踏步走上来,楼梯嗵嗵山响,他把包着人头的布袋扔在脚下,又恢复了平日的神色,“白胡子老汉死了。”
“阿爸——”
黑眼睛少女撕心裂肺地大叫一声,扑在布袋上,嚎啕痛哭。
后来,斯琴塔娜拒绝了大头喇嘛的挽留,离开公婆泉,搬到了火烧井东边的神泉。现在,大头喇嘛就是要去神泉,他打算再看上她一眼。
白骆驼缓步走上一片丘陵,眼前是水域广阔的沼泽地,已到了结冰的时候,茂密的芦苇丛中透出斑斑点点的冰面。远处的地平线,惨淡的星光与湖面呼应,透露出神秘的弧光。沼泽地浸出透人骨髓的寒意,芦花摇曳,发出奇特的声响。这一切都令他联想到故乡科布多。还记得吗?那科布多河、布彦图河与伊格尔河汇集的阿拉克湖泊,那是他最初闯入的广阔天地啊!
在他五岁那年,父亲第一次把他扶上马背,母亲在身后呼喊着,那匹顽皮的马驹,故意不走正道,却顺着科布多河斜斜奔向阿拉克湖,初上马背的他惊叫着,硕大的脑袋随着单薄的身子前仰后合。不知什么时候,已被驮进了芦苇丛,芦苇叶被他和马驹弄出一片哗啦啦的声音,尖利的叶片擦过他嫩嫩的脸蛋、胳膊和大腿,划出多少道血口子啊,那新鲜、红润的血珠,发出了滚烫的、腥甜的味道,引得蚊蝇都围着他打转。他被这一切搞得晕头转向,实在不明白,这就是父亲谆谆告诫的生活真谛,或者是人生的开端?实际上,他还不知道,庄严的承化寺通过金瓶掣签,已确定他是转世灵童——活佛,尊号是诺彦呼图克图。此次也是初次驾驭马匹的活动,不过是人生旅途的热身而已。
一个晴朗的早晨,百灵鸟高歌之后,随着鼓号铙钹鸣响,在科布多办事大臣的陪同下,承化寺众多喇嘛排成整齐的队伍,恭迎转世灵童。后面,缭绕的香火间,虔诚的信徒匍匐在地,抑扬顿挫的诵经声响彻天地。这一刻,年仅五岁的丹宾嘉禅突然明白:我就是神圣的化身!我就是芸芸众生的精神所在!我就是至高无上的呼图克图!
于是,五岁的转世灵童毫无怯意,竟背抄双手,阔步走向金顶大轿,毫不推辞接受了虔诚的信徒们乃至父母的顶礼膜拜。
“噢呀——”
承化寺的住持高僧乃至见过上一世诺彦呼图克图的僧侣们从内心发出了惊叹:伟大的佛祖啊,你终于向世人显现了真身,这个大头的孩子,的确是承化寺的转世灵童啊!
就在金顶大轿离地的刹那间,丹宾无意间瞄到了阿拉克湖的芦苇,那滚烫的、腥甜的血珠的味道就又散发出来了,瞬间,年幼的活佛竟冒出一个奇怪的念头:难道此生本活佛要与血与火度过一生吗?
四
现在,丈余的芦苇包围了他,干燥、冰冷的叶片又划过他的脸颊和胳膊,那刀片似的叶子再也割不破他的皮肤了,大头喇嘛禁不住微微一笑,我的身体就像千年的胡杨树皮了,小小的芦苇叶那能划破厚实的树皮呢?以后呢?我会化作一缕轻烟,袅袅升向天国,到那时,叶片呀、刀枪呀都没法伤害我了,一缕轻烟嘛,还在乎什么冷热交替、喜怒哀乐或者生离死别吗?什么都不怕了。
沉稳的驼掌踏上一处土丘,从这里向东望去,一条自北向南的便道隐约延伸在芦苇丛中。沿着这条道路可以到达酒泉,继续走的话,还能去西藏的布达拉宫。一棵高达丈余的梭梭枝干峥嵘,独傲草滩。看到它,发生在去年这会儿的往事又涌上心头。谁能相信,那次的劫道事件,竟改变了大头喇嘛人生信念。
民国十一年的11月,独辫兴奋地禀告,哲布尊丹巴那条老狗的日子难过了,北边的大狗熊不喜欢他了,他怕自个的私房钱被人夺去,打算把金银财宝、枪支弹药弄到西藏去,请达赖或班禅代他看管,“佛爷,光金银就四百驮呢。”察苏台的蓝眼珠子闪闪发光,“还有一百驮枪弹。”大头喇嘛禁不住替他担起心来,真怕俩蓝眼珠子冲出眶子,飞到天上作一回星星。
话是跟酒泉人学的,本来是对孩子的昵称,从他嘴里出来却没丁点亲切感。七十来个衣衫肮脏的喇嘛押着五百多峰骆驼,一步步钻进了套子。
“打!”
独辫高大的身躯猛地挺立起来,随着他歇斯底里的呐喊,手腕一抖,一束火光从他乌黑的枪口喷出,道尔吉睁大尖利的眼睛,双手捂住喷血的胸口,仰天倒下马去,喷出的鲜血溅到了后边惊蹿的骆驼身上。也许是距离过近,伏击者喊叫着就和敌人纠缠在一起,枯黄的芦苇被拥挤的人畜践踏后,腾起冲天的黄尘,尘埃里已分不清敌我。
狼扯疤早已扔了枪枝,挥舞马刀冲进人群,喇嘛们何曾见过这般尊容,立马成为无组织无纪律的野狗。没门牙骑士走风漏气叫喊着,趁势打倒一条飞毛腿。其其格爬在土墩后,汗水与尘土糊脏了她端庄的脸蛋,紧张地注视着混战的人们。突然,一个外蒙古喇嘛抡圆马刀卑鄙地想偷袭正在跃马酣战的活佛,其其格尖叫一声,搂响了火枪,与此同时独辫的驳壳枪也喷火了,那家伙就像抽筋的野驴摔下马来,立刻被人畜踏成肉泥。丹宾嘉禅回过头来冲她一笑,“好样的,会杀人了。”受到鼓舞的少女跳将起来,照着一个小喇嘛抡起枪托,这回运气可不太好,小喇嘛躲过袭击,按倒少女,从靴筒抽出猎刀凌空就要刺下,其其格绝望地惨叫一声,那小喇嘛却酥软地爬在了她身上,以为已进入天国的少女睁开眼睛,看见黄胡子正从死尸背上拔马刀,“元旦哥!”她激动地喊道,黄胡子没有答茬,返身劈翻一条大汉。
“立刻投降!”
大头喇嘛立马高坡,左轮手枪指向敌人。
“投降!投降!”
芦苇丛里的古道上,到处响起杀气腾腾的喊声,已无路可逃的送货人终于放下了武器,五百余驮金银财宝和枪枝弹药被搬进了大头喇嘛城。
五
后来呢?后来丹宾嘉禅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似乎一个晚上,桀骜不驯的大头喇嘛真的立地成佛了。大多时间是在诵读佛经,左轮手枪却成了摆设,常常独自徘徊斗室,神情痴呆。
“我死后弟兄们去哪儿呢?”
大头喇嘛长长吐口气,从芦苇丛中抬起头来,看见北边的天上悬挂着七颗星星,如同一把巨大的勺子,围绕着北极星旋转,在清冷的夜空里,愈发显得明亮。他一下明白了:不管这星星组成的勺子咋个运转,它都离不开北极星。流浪汉浪荡得再远,心理挂念的依旧是家乡的山山水水。那么自己死后,流落马鬃山的信徒们理所当然回到故乡。就朝那个勺子的方向走吧,他想。朝勺子方向走,就不会迷路,就能回到科布多老家。老家嘛就有肉吃,故乡的勺子里咋也不会缺了儿女一口肉汤。就这么想着,还真闻到了熟悉的味道,起初还不敢相信,但肠胃已经痉挛起来,唾液充盈了嘴巴。二十来年漂泊的经历告诉他,嘴巴和肠胃是不会骗人的。
走出芦苇丛,不远的梭梭林里,有一座白色的蒙古包,旁边是梭梭柴扎成的羊圈。大约是听见了不速之客的脚步,一匹黑骏马正抖鬃嘶鸣,牧羊犬冲着这边狂吠。蒙古包的门帘子被掀开了,大头喇嘛看见了身穿合体白袍盛妆打扮的黑眼睛姑娘,还有她身后燃烧的梭梭柴炉子,红色的火焰,舔着一口黄澄澄的铜锅,锅里的羊肉正在翻滚,那熟悉的煮肉熬汤的香味,就是从那里飘出的。
大头喇嘛驱赶着狂吠的牧羊犬,笑呵呵地对女主人说:“东家啊,汉人常说石头砌墙房不倒,喇嘛进家狗不咬。你家的战马和猎犬可不得了,连活佛都不放在眼里。”黑眼睛姑娘甜甜地笑了,一声断喝,于是黑骏马停止了嘶鸣,牧羊犬绕着女主人和客人摇尾戏耍。在漆黑的黎明,炉火显得格外耀眼,摇曳的火光里,他和斯琴塔娜面对面站着,彼此反倒不知该干什么了,就这么直盯盯看着对方,老半天丹宾嘉禅才说:“过得好吗?”牧羊女的嘴唇颤抖着,两行晶莹的泪珠滚落下来,大头喇嘛心头一阵酸楚,情不自禁伸出双臂,打算把牧羊女揽进怀里,双手却迟疑一下,停在了半空,姑娘红盈盈的嘴唇溢出一声叹息,便扑进他宽厚的胸膛……
梭梭柴炉子的火焰在呼呼作响,热气把大头喇嘛的泪水熏了出来,牧羊女帮着脱去羊皮大衣,用袖口擦擦他的泪水,孩子气地一笑:
“佛爷哭了,是怕我这头母狼吧?”
“不,”大头喇嘛笑了,“本佛爷们营寨是狼窝,吓得姑娘不敢去……”
“嗯——”牧羊女娇嗔地一跺脚,“佛爷最坏!”
“哦嗨?”大头喇嘛故做惊讶,“大胆刁民竟敢当面侮辱神灵,你就不怕万劫不复?”
“哼?!有普渡众生的佛爷在此,我还怕沉沦无边的苦海?”斯琴塔娜笑起来,虽然没有笑出声音。她仰起了脸蛋,饱含着幸福的笑意。阴影从她的眼窝里移开了,黑黑的眼珠闪烁着光芒,里面清晰照出丹宾像的影像。
大头喇嘛轻轻摇摇头,心想我都自身不保了还能普渡谁呢?黑暗中,西北风均匀、有力的吹过蒙古包顶部,如同湖水的波浪拍击着岸边。他在火炉边盘腿坐下,先喝下牧羊女敬献的一碗驼奶酒,不待主人招呼,拿起勺子在铜锅里搅动。走了这么长时间的夜路,还真饿了,很想立马喝口香浓的肉汤,但肉汤那么烫嘴,他有些不知所措,就那样不可待地拂着热气。黑眼睛牧羊女吃吃笑着,干看他着急,就是不帮忙。大头喇嘛无可奈何摇摇头,便放下铜勺。斯琴塔娜笑盈盈地取出盘子,满满盛上一盘肉,双手递上一把餐刀,“吃吧,我的佛爷。”吃下第一口肉,大头喇嘛才感到更加饥肠辘辘,“就你一个人,平日也煮这么多肉?”“才不呢,我知道佛爷来才煮的。”“哦,你也变成能会算的佛爷了?”“昨天百灵鸟叫了,我就知道佛爷要来。”“哦,是吗?”他心不在焉应着,鼓胀着腮帮子,嗓子里传出咕噜咕噜的声音。牧羊女跪坐在大头喇嘛的身旁,仰望着他贪婪的吃相,小巧的嘴发出一阵含混的喉音,起初大头喇嘛还以为是斯琴塔娜的叹息,但这喉音在持续地延伸,舒展,渐渐地,成为悠长的咏叹。
作为终年颠簸于原野不停寻求栖身之所的马背民族,很少有欢快的曲调,她的子民的牧歌里总是缠绕着忧伤的旋律。而这一切从一个失去亲人有家难回的牧羊女娇嫩的嗓音倾诉出来,就显得尤为哀伤了。当她重复吟唱第二遍的时候,大头喇嘛低沉、沙哑的歌喉也加入进来,这使得原本就很伤情的长调听起来更加粗犷、也更加悲凉了。
六
羊油灯发出稀薄的光芒,牧羊女仰望着他痴迷的神态,泪珠从她黑黑的眼睛里淌出来。牧羊女小巧的嘴唇紧紧地抿着,泪水顺着鼻翼两侧的纹路流过了嘴角,挂在圆润的下颏,这使得她的哭声显得格外压抑。看到娇小的姑娘如此难过,似乎是荒郊僻野中无助的小动物,大头喇嘛也跟着难过起来。推开盘子,顺势在膝盖上擦去双手的油腻,伸出袖口帮她试去滚落的泪珠。他的举动非没有缓解牧羊女的悲痛,反而使她压抑的哭声更有力了。望着美丽动人的姑娘在自己面前无所忌惮地哭泣,大头喇嘛的心不在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姑娘的泪水滚落着,如同珍珠闪烁着晶莹的光点。修长的身子在白袍里抽搐着,就像一头艰难喘息的小白羊。对于自己的袖口未能释去她满怀的悲怆,大头喇嘛深感疑惑,就想她的哭泣如此无以复加,大概不仅仅是联想到了相依为命的白胡子老爹,可能还有更伤心的事吧?那到底是什么伤心事呢?她可从来没有告诉过自己。在他心目中,斯琴塔娜与其说是个不称职的刺客,毋宁是还没长大的娃娃。如她说过的,自小她就是只野山羊,野山羊会这么脆弱吗?
这么想着,大头喇嘛才发觉自己和牧羊女挨得太近了,几乎眼对鼻子了。牧羊女仰着头,黑黝黝的眼珠直盯着他,泪蛋蛋还挂在脸颊,红辣子般的嘴唇微微张合着,呼出热乎乎的气息,湿润了他干燥的嘴巴。犹豫一下,一双大手就贴在她白里透红的脸蛋。姑娘的脸蛋被泪水浸透了,摸上去凉凉的,手心触到泪珠的时候,似乎听到了轻轻的哧哧声,就跟泪水滴溅在沙子上一样。大头喇嘛明白,长年的流浪生涯自己的手心已非常干燥了,如同老胡杨树皮,还裂出很多口子。姑娘的泪水不仅湿润了他的掌心,连他的心田也被滋润了。
牧羊女不再流泪了,但她低哑的啜泣并未停止,啜泣声很容易和喘息混淆,她微微启合的红红的嘴唇,紧紧含住了大头喇嘛的耳垂,呼出的热气把他的脸颊、脖子打湿了,合糊不清地说了句什么,大头喇嘛却明白了其中的意思。
戈壁滩刮过一阵狂猛有力的风,这风来得显然不合时宜,听起来令人不安和忧郁。大头喇嘛侧耳听着,听听是否夹杂着刺客的马蹄声。牧羊女探起身来,重复说了句什么。她的声音很嘶哑也非常温柔,压抑着说不清的急切。大头喇嘛回过神来,就着稀薄的羊油灯光,看到了牧羊女再次涌出的满眼的泪水,想到她对自己如此的依恋、亲昵,而自己心中依旧怀念着的斯琴,就觉着如此压抑自己的情感,是不是过于伤害了牧羊女的心呢?这样想着,心头就涌上一股说不上的愧疚与难过。然而自己是即将踏上死亡之旅的人,又有啥理由占有牧羊女的身心呢?她毕竟比自己小得多,人生的路才刚刚开始啊。他搂住牧羊女的身子,轻轻放倒在羊皮褥子上,闻着姑娘身上淡淡的奶酸味,凑在她的耳边,低低说:“我只是看你的!”牧羊女浑身一颤,红盈盈的嘴唇一咧,倒吸了口气,遭受了重击似地哭出声来。
尾声
民国十二年农历十月初八清晨,刺客契丹吉宁装病,请大头喇嘛亲自诵经驱灾。
听老人讲,那天大头喇嘛走进了刺客的毡包,契丹吉宁立刻单膝跪在地上,他的同伙则拱手躬身站在门旁,齐声道;“佛爷!”就在大头喇嘛弯腰摩顶的刹那间,契丹吉宁从靴筒拔出了匕首,一下刺进了丹宾嘉禅的左肋,如注的鲜血喷涌而出,大头喇嘛抓住了刀柄,怒目喝斥:“畜牲,干这点活还不利索。”猛一使劲,连刀把也捅了进去,如山的身躯轰然倒下。三个刺客面面相觑,满脸都是虚汗。老半天,契丹吉宁才缓过神来,“妈的,快发信号呀!”
大门发出闷雷般的声响,500多个剽悍的蒙古骑兵挥舞弯刀,呐喊着冲进城寨,大头喇嘛城陷落了……
半年后炎热的夏天,张团总乘坐骡轿回到了马鬃山。老汉吸着水烟袋,捋着三缕长须,像庄户人察看庄稼似的,在大头喇嘛城转了很长时间,“也是个人物呢。”他呐呐自语,然后对众人说;“该务甚就务甚,没甚看的。”
1934年,为勘探绥(远)新(疆)公路,瑞典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率队途经额济纳土尔扈特旗。那年的1月底,勘探队路过公婆泉,还专程造访了这座废弃的城池。这天刚刚下过雪,西北风撕扯着依旧密布的浓云,寒气逼人。面对显赫一时的废墟,赫定博士感慨良久。后来,在他的《丝绸之路》一书中回忆道:
“丹宾喇嘛,人称‘假喇嘛’。他就住在这座坚固的城堡中,向过往的商队勒索税钱,十二年前,喀尔喀蒙古人袭击了这里,杀死了丹宾喇嘛。……”
就在车队启程时,天上又飘起了雪花。猛然间,斯文·赫定似乎听到了悠扬的驼铃,他转过身来,惊诧地看到,寂寥的天地间,远远的戈壁滩,一个蒙古女人骑一峰雪白的骆驼,正缓缓向这边走来。在这刹那间,博士的心灵被震撼了:她靠什么活呢?生命太伟大了,太顽强了,要知道,这里就像月球表面一样荒凉啊!带路的土尔扈特人告诉洋人,她就在附近放羊,老骑着白骆驼到大头喇嘛城转悠。还说,她的眼睛黑黑的。
(作者: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档案史志局)
- 年鉴刊物上一篇:【方志大观】修志问道 尽责圆梦
- 年鉴刊物下一篇:【史海钩沉】打响蒙古族抗日第一枪的民族英雄陶格陶胡
- 声明: 转载请注明来源于《内蒙古区情网》官方网站














 当前位置:
当前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