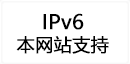第六期
- (卷首语)修志为用 服务社会
- (志鉴论坛)当代方志文化的构建及其意义
- (志鉴论坛)人物传可记述传主的文化艺术修养
- (志鉴论坛)志书称谓七议
- (专稿)百年『世界心脏』的形象描绘--元朝诗词中的元上都
- (专稿)毛泽东与徐悲鸿的交往
- (史海钩沉)中央红军长征在定边(连载)
- (史海钩沉)归化城的『六陈行』
- (史海钩沉)功勋卓著的卓盟纵队
- (盟市园地)哈达与蒙古族文化
- (盟市园地)『阿拉善』地名由来说
- (盟市园地)阿拉善和硕特旗与定远营的历史渊源
- (盟市园地)探秘黑城
- (旧志述评)民国赤峰县杂事考--伪康德四年《赤峰县地方事情》读后记
- (大事记)内蒙古大事记(2011年11~12月)
- (珍珠滩)凉城行
- (珍珠滩)读月亮(外三首)
- 旧志简介
- (志鉴动态)自治区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杨泽荣到阿拉善盟调研
- (志鉴动态)锡盟对第二轮修志工作进行督查
- (志鉴动态)阿拉善盟档案史志局
- (志鉴动态)《内蒙古自治区志·教育志》(稿)评审会召开
- (志鉴动态)《内蒙古自治区志·人民代表大会志》举行首发式
- (志鉴论坛)志书称谓七议
- 发布时间:2012-05-07
- 来源:本站原创
称谓,就是名称,如人名、地名、事件名、物品名、职衔名等等。在志书的记述过程中,必然要运用到各种各样的称谓。用之得当,可以使志文合乎规范,提高质量,也可使读者一目了然,省去一些麻烦;用之不当,效果恰恰相反。如何在志文中使称谓使用得当,本文谈以下七点。
一、采用通用的
通用的,即通行的,流行性大的,知名度大的,广为人知的。一人、一地、一物、一官职,往往会有几种称谓。在志文中,就要采用通用的、流行性大的、广为人知的一种。这似乎是人所共知的,不必加以谈说,其实不然。就拿一个人来说,除了名字以外,还会有字、号,有的人以名行(知名),有的人以字行(如蒋介石),有的人以号行(如杨虎城)。古人诗文中,还往往以某人的家乡地名或官职,作为某人的代称,如家在凤洲的称凤州,做过吏部尚书的称天官。之所以如此,或为表示尊敬、庄重,或为显得文气、高雅。在一定的时间、地域、范围内,读者一看便知其所指为谁。但时间、地域、范围一变,就难知其所指,非进行考证不可。就连方志大家章学诚的文章中,此类毛病也在所难免。正如仓修良先生所说:“章氏在许多文章中都批评前人行文很不规范,其实他自己亦是如此”。古今名人大多使用字号,一般很少直呼其名,但查找起来可就麻烦了。尽管有多种名人字号辞典,历史上不同朝代人物,会有十多个人在使用同样一个字或号,于是有时候很难辨哪一位是你所要查找的人物。有许多并非有名的人物,辞典也不收录,这就更难找了。还有许多则是用地名、官号来称呼人名,如万甬东、胡德清、徐昆山、潘济南等。以官号名者如梁制军、周内翰、谢藩伯、徐学使、翁学士等等。影响比较大的自然容易识别,影响小的麻烦就大了,因为任何名人辞典都无从查找。所以,为了使广大读者和以后的读者能够顺畅地阅读志文,不给他们制造麻烦,志书中的称谓应该采用通用的、流行性大的、广为人知的一种。在特殊情况下(如人物对话中或记述特定时段、环境的事),需要用冷僻的、流行性不大的称谓时,也应加上注释。渭南民间曾称井岳秀为井十,称樊钟秀为樊老二,称麻振武为麻老九。有的志稿在记述涉及这些人的历史事件时用了他们的异称,却没有注释通行姓名,使读者非常费解。
二、关于规范性与俗称
一个人、机构或物,往往有几个名称,有正式名称,也有除此之外的俗称。同一动、植物,异地异名的现象就非常普遍。马铃薯,又叫山芋、洋芋、土豆、山药蛋,陕北还叫蛮蛮;雉,又叫野鸡。中草药,同物异名、同名异物的现象,不胜枚举。在志文中,若不采用正式的、规范的名称,势必产生混乱,使读者误解。早在战国时期,荀子就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这里的“约之以命”则是广大人民群众形成共识,产生规范的名称。志书是严肃的资料书,对一切人、事、物,均应采用规范的、正式的、准确的名称。例如志书的人物表中,记载某人是“国民党军第×军军长”。这个“国民党军”,就不是规范的、正式的称谓,只是表明了其归属。国民党的军队自从1925年7月成立,直到败退台湾,正式名称都是“国民革命军”。再例如,“新中国成立后”,其中的“新中国”就是俗称,应该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等等。
我强调使用规范的、正式的称谓,这只是就普遍的、大多数或绝大多数而言,并不是说俗称一概不能用;凡事都不能绝对,都有个别的、例外的情况。例如“黄埔军校”,这并不是它的正式名称。它的正式名称是“陆军军官学校”,因其校址在广州黄埔长州岛,世称“黄埔军校”。这个名称虽然不是正式名称,但在社会上已经产生了类似正式名称的效应,也算一种“约定俗成”吧。若在志书中记载某人“系陆军军官学校第×期毕业生”,反倒叫人觉得陌生。又如孙中山,他名文,字德明,号日新,又号逸仙;因进行反清革命时化名中山樵,遂世称孙中山。这虽不是他正式的名、字或号,但已被社会接受,若无特殊需要,还是称“孙中山”为好。若因为不是正式的名、字、号,在志文中涉及它而不用,就显得迂腐可笑,不近情理。说道这里,想起一个笑话。说是有个腐儒走到河边,为河中涨水不可涉过而发愁。旁边一个人向他说,河面不太宽,一跳就过去了。腐儒就双脚并拢一跳,结果掉到河水中去了。旁边那人笑他怎么双脚并拢,而不先把一只脚向前跨。腐儒埋怨那人道:“单足为跃,双足为跳。你叫我跳,没叫我跃呀!”撰写志文时,在总体上把握规范、正式的前提下,对特殊情况,具体分析,具体对待,这才符合辩证法,才不至于闹出笑话。
三、关于时段性(时代性)
时段性,就是历史性。任何事物,都存在于历史长河中的一定时段之内,与它们紧密联系着的名称(称谓),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时段性。例如,现在记述“×××(1910—1980),韩城市人”,这就不对。因为韩城1984年才由县改为市,其人从生到死,都不存在“韩城市”这个建制;而应记述为“×××(1910—1980),韩城县(今韩城市)人”。如果记述为“×××,1910年出生于韩城市”,那更不对了,而应记述为“×××,1910年出生于韩城县(今韩城市)”。又例如,记述某人“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就不对。因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个名称,1925年才产生,此前该组织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团”。再例如,记述某人“1930年到北京”,这是不对的,因为1928年改北京为北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平复称北京。此后若再使用“北平”也是错误的。同样,关于人的职衔的记述,同一职衔,不同的时代就有不同的称谓。例如县级行政长官,隋、唐称县令,明、清称知县;等等。就某一个人来说,他一生所任的几种或多种职衔,也有严格的历史时限,丝毫马虎不得。例如胡宗南,“1942年1月,代理军委会委员长行营西安办公厅主任,3月,再兼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11月代理司令长官。1945年1月12日,赴汉中正式就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在一篇人物传记中,若在不同的年月几次出现胡宗南,他的职衔就会不尽相同。在交代他的职衔时若大意,就会出差错,不可不小心谨慎从事。
四、关于全称与简称
在志书记述中运用事物的全称,可以显得庄重、规范、正式、准确;但若处处使用全称,也会使行文累赘,于是有运用简称的必要。“八路军”全称是“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八路军”;“新四军”全称是“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在志书记述中,涉及到某人某年参加八路军,某人某年参加新四军,不必要用其全称,用“八路军”、“新四军”就行了。在何种情况下用全称,何种情况下用简称,这就要看具体的语言环境(上下文的情况)了。一般地说,简称类似于语法中的代词,如“他”、“它”。运用代词,必须有“前行词”,即“他”或“它”的名称。否则,读者读到“他”、“它”就不知所指了。“我今天见到张三,他的身体很健康。”“我刚读完《红楼梦》,李四就把它借去了。”这两句话中“张三”就是“他”的“前行词”;“《红楼梦》”就是“它”的“前行词”。试想如果没有前行词,读者如何准确理解这两句话的含义?同样道理,对一些名称,特别是那些知名度不是很大,或只流行于某行业某地域的事物名称,若其在一篇文字中只出现一次,就必须用全称,后文重复出现时,才可以用简称。这里牵扯到缩略语,如“三反五反”、“四清运动”、“五讲四美”、“五好家庭”等等。今天的读者一看,似乎都知道只流行于某行业、某地域的缩略语,更应如此。撰文者一时疏忽或偷懒,就会给后人留下难解的谜团。
五、关于称谓中几个成分的顺序
笔者在阅读志书、志稿和其他书籍、文章的时候,往往发现称谓中一些成分的位置放置不当,粗略看去,似乎可以,仔细辨析,就有问题,影响文义的表达,影响语言的科学性、严密性和准确性。
其一,“原”、“前”的用法或位置不当。有县志稿记述:“×年×月×日,原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来×县……”。经查证,当时这位省委书记没有退休或调走,正是以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的身份来×县视察工作,那怎么能用“原”字呢?这种理解是错误的,因为所记载的是以往某年的事,并不是修志之时的事。有志稿记述:“×年×月×日,原×县人民政府县长×××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这句话中的“原”字位置不当,应该是“×县人民政府原县长”才确切。因为“×县人民政府”还存在,不能在其前加“原”字,彼人是“县长”职务不存在了,在“县长”前才可以加“原”字。有志稿记述:“前县志办公室主任×××任第二轮县志主编”,这句话中“前”字位置也是不对的,应该是“县志办公室前主任”。因为县志办公室仍然存在,只是该人的“主任”职务不存在了,属前任。正如现在对戈尔巴乔夫,可以称“前苏联总统”;而对尼克松,不能称“前美国总统”,应称为“美国前总统”。
其二,用以限制某词的数量词与它所限制的词距离太远。有的志稿记述:“×渠通水后,解决了一个全县人民渴望了多年的几十万亩旱原农田灌溉的大难题。”其中的“一个”是数量词,“大难题”是它所要限制的中心词,中间隔了那么多的字,实觉别扭。把位置原应在后的词移到前面,在语法上叫“前置”,起突出与强调的作用,在上面这句话中“一个”没有突出与强调的必要,还应保持它原来应在的位置。所以,这句话应调整为“解决了……一个大难题”。又如,“进军途中,遇到几名打了败仗成为散兵游勇、正在乡间逞凶作恶欺侮老百姓的日军士兵。”其中的“几名”是限制中心词“日军士兵”的,但距中心词太远,就调整为“遇到……几名日军士兵”。
其三,人大、政协名称中的届次的位置不当。全国人大,规范的称谓是“第×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政协,规范的称谓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届全国委员会”。人大,届次在名称前;政协,届次在名称后。而在志稿中,往往出现该前却后、该后却前的混乱现象。
其四,职衔的位置不当。有志稿中记述“×××在朝鲜战场上,生俘了美军鲍威尔上校”,类似的称谓“×××校长”、“×××主任”、“×××团长”等等。这种把职衔置于姓名之后的写法,在志书中是不适当的,应该一律把职衔放在姓名之前。放前或放后,似乎没有什么差别,但仔细品味鉴别,含义不同。职衔在前,书面语成分多;职衔在后,口头语成分多,而志书采用书面语,不采用口头语。职衔在前,属中性记述,不带感情色彩;职衔在后,带有亲切的感情色彩,而志书的语言,要求客观地记述资料,不要求带感情色彩。
六、关于称谓的感情色彩
前面提到,志书的语言,要求客观公正地记述,运用中性的词汇,一般不带感情色彩。这不是说志书不要政治倾向性。志书的政治倾向性,是通过取材和记述,寓事理于事实之中。对“匪”、“盗”、“敌”、“友”、“伪”之类充满强烈感情的称谓,不是完全拒绝使用,而是要使用得准确。不同的历史时期,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上,赋予这些词的含义各有不同。一部志稿在记述一位封建官员的政绩时说:“平定了著名盗匪×××之乱。”经查有关史料,这名所谓“盗匪”是不堪忍受封建当局的欺凌压榨而官逼民反率众起义的领袖。这就是个原则问题,不容忽视。说轻点,是对史料没有弄清;说重点,就是立场问题。即使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立场,不同的历史时期,“敌”、“友”的所指也有不同。有的志稿记述抗日战争时期的事,把国民党当局及其军队都称为“敌人”,这就不对了。在当时,只有日寇、汉奸、伪军(投降日军的中国兵)可以称为敌人。国民党政权及其军队中,即使是制造与八路军、人民政权摩擦的顽固派,也只称其为“顽固派”而不称“敌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把在国民党政权中任过职的人员统称“敌伪”人员。于是在有的志稿中,把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军政官员都给冠以“伪”字,“伪县长”、“伪保长”等等。这是不恰当的。历朝历代的封建政权都不是人民的政权,难道都要给冠以“伪”字?所以对国民党政权中的官员,只称为“县长”、“保长”等就行。对汪精卫等汉奸政权中的官员,可以冠以“伪”字。
七、关于称谓的角度
撰写志稿时的角度恰当与否,关乎记述是否客观公正的问题。志书要求使用第三人称(他),而不要求用第一人称(我),就是要求修志者站在史官的角度,而不是站在史实的参与者的角度去进行记述。司马迁的《史记》中有一些“我”,仅《鲁周公世家》中,就有“齐伐取我隆”,“齐伐我”、“楚伐我”等,是他在整合各国史料进行记述的过程中,没有把原来的称谓改变过来,可以说是疏忽,是瑕疵。今人修志,不必效仿。现在有的志稿中,把引用原话与转述其意中的称谓分辨不清,互相混淆。有志稿中说:“×××慷慨激昂拍着胸脯发誓说‘他全心全意跟着共产党,一辈子干革命,永远不变心!’……”这句话中的“他”应该是“我”。若保留用“他”那就不是原话,而是转述其意,那就不能使用引号了。另外,一些志稿对“以来”用法不当。“以来”为“方位词。表示从过去某时直到现在的一段时间。有部志稿中用了不少“以来”,但其“现在”(下限、立足点)不明确,有的似乎到了该志下限,有的却在该志下限以前。如一部下限为2006年的志书,为一个去世于2000年的人立传,说他“任×××中学校长以来……”这里的“以来”就颇有年终或某阶段工作总结的味道,与该志的下限不符,不如改用“后”或“期间”。“以来”在志书中虽然不能说完全禁用,但牵涉到具体时段的,最好写明某年至某年。这样,才不致下限模糊,费人猜测。
以上所谈,仅属管见;如有不妥,敬请赐教。
(作者:陕西省渭南市地方志办公室)
- 年鉴刊物上一篇:(盟市园地)探秘黑城
- 年鉴刊物下一篇:(盟市园地)阿拉善和硕特旗与定远营的历史渊源
- 声明: 转载请注明来源于《内蒙古区情网》官方网站














 当前位置:
当前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