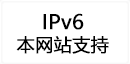第六期
- (卷首语)修志为用 服务社会
- (志鉴论坛)当代方志文化的构建及其意义
- (志鉴论坛)人物传可记述传主的文化艺术修养
- (志鉴论坛)志书称谓七议
- (专稿)百年『世界心脏』的形象描绘--元朝诗词中的元上都
- (专稿)毛泽东与徐悲鸿的交往
- (史海钩沉)中央红军长征在定边(连载)
- (史海钩沉)归化城的『六陈行』
- (史海钩沉)功勋卓著的卓盟纵队
- (盟市园地)哈达与蒙古族文化
- (盟市园地)『阿拉善』地名由来说
- (盟市园地)阿拉善和硕特旗与定远营的历史渊源
- (盟市园地)探秘黑城
- (旧志述评)民国赤峰县杂事考--伪康德四年《赤峰县地方事情》读后记
- (大事记)内蒙古大事记(2011年11~12月)
- (珍珠滩)凉城行
- (珍珠滩)读月亮(外三首)
- 旧志简介
- (志鉴动态)自治区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杨泽荣到阿拉善盟调研
- (志鉴动态)锡盟对第二轮修志工作进行督查
- (志鉴动态)阿拉善盟档案史志局
- (志鉴动态)《内蒙古自治区志·教育志》(稿)评审会召开
- (志鉴动态)《内蒙古自治区志·人民代表大会志》举行首发式
- (史海钩沉)归化城的『六陈行』
- 发布时间:2012-05-07
- 来源:本站原创
俗话说,“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记者是生于黄土高原的北方人,平时最爱吃面食,因此,经常光顾居家附近呼市团结小区市场周边的粮油面食店,同时,也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在这一带经营粮油商店的老板倒有不少操着晋中、晋北一带的口音,进一步采访得知他们当中大部分人是晋商的后裔,多半以忻州、祁县、平遥、文水籍人居多。由此,依稀想起上中学时,父亲说过,他那从粮食局退休没几年就去世的伯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曾在归化城山西粮商、代州人孟维峻开的“六陈行”—— “复元永”面铺当过伙计。那么,归化城 “六陈行”的由来,以及这一行在过去是如何经营的,恐怕如今没几个人能说得清。为此,笔者专门查阅了有关史料,欣喜地发现不但谙熟于呼和浩特商业掌故,而且还曾与昔日归化城著名的“六陈行”——“复元永”掌柜孟维峻有过交往的山西崞县人(今原平市)贾汉卿先生对此有详细的记忆,从而了解到当年的“六陈行”曾经给归化城这座塞外名城带来市场活跃和商业繁荣背后的种种内幕……
归化城的“六陈行”及其由来
“六陈行”是华北商人对经营粮油行业的习惯用语。《三字经》上所记载的“稻粱菽,麦黍稷,此六谷,人所食”,就是它的最初含义,因这六种粮食可以长久储存之故,所以就有了这一称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六陈行”曾经普及山西、陕西、察哈尔、绥远。
归化城的六陈行,是康熙中叶随着汉民增多与小型集市的出现而产生的。在归化城最早经营“六陈行”的商号是一家叫做“天怀祥”的面铺。之后归化城的“六陈行”有德合荣、源德魁、和顺兴、恒裕泰、三盛荣、三成玉等40多家。当时担任西行乡总掌柜的有宁生、王永、曹皇升、梁福喜等44人。至乾隆年间,碾米磨面系属一行,统称为面行。而碾房附带的缸房、油房,也都酿榨白酒与葫油,大量上市,供人们需用。
“六陈行”组织——福虎、青龙、六合社
嘉庆年间,商业发展,各行各业有了“社”的组织。“六陈行”的营业性质有所区别,官府组织了福虎社和青龙社,一般面铺属于福虎社,社址设于玉皇阁;碾房与缸房属于青龙社,社址设于财神庙。当年福虎社成立后,按照地方习俗,每年阴历六月初六,在玉皇阁演戏酬神,青龙社也在二月初二在阳沟沿搭台唱戏。这项活动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以后。
六合社是”六陈行“的碾官、磨官与缸房、油房的大二师傅等组成的,每年各季工人的工资,都由该社来决定。凡是参加六合社的工人,依照规章,不得任意加班,为资方利用。每到深夜,派人检查,如有违反社规,破坏工人组织者,查获后予以严厉处分。每年夏季,六合社也在小东街关帝庙演戏三期,一切开支,由入社工人共同负担。民国10年前后,六合社宣告解体。
“六陈行”的极盛时期
清咸丰年间,因银根奇紧,周转困难,开张的面铺有所减少;而一些碾房将所存小米运往托县河口,转售于晋西一带的粮商,南下后不时开盘,尚见活跃。
光绪九年(1883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洋商西来,疯狂掠夺各种物资。当时归化城的“六陈行”,除一部分老字号如涌泉龙等继续存在外,新开张的面铺、碾房与缸房、油房计有100多家,户量陡增,呈现出一种外强中干的不正常景象。
辛亥革命以后,归化城曾易名归绥,当时除个别字号收庄和歇业外,大部分存在。到民国17年,开张的面铺、碾房与缸房有义记义川会、复兴昌、德和兴、天裕亨、蔚和成、昌兴隆、元聚厚、万盛昌、吉善堂、意生德、万亨成、德义成、兴泰成、万庆恒、义和公、聚盛馨、天义公、义生泉、昌兴号、庆和祥、义和亨、瑞和谦、德中诚等140余家,可谓米面业的极盛时期。
“六陈行”的经营
当年归化城的“六陈行”,大多数是各地的资本家拿出一定的资金,准备设施,而后开张的,经济实力比较雄厚。如包头复字号开设的德兴长、大御史巷刘柱开设的天裕亨、罗家营子高家开设的复义泉、骑兵师长郭凤山等开设的复义昌以及山西祁(县)太(谷)帮、忻州帮与代州帮、崞县(今原平市)帮开设的天义公、复盛元、万盛兴、德和兴、庆隆茂、三和兴、复兴泉、复顺公、聚隆昌、复顺泰、西盛茂、丰盛魁、天和兴、天兴魁等,都是操纵市场的面铺、碾房与缸房,尤其是天义公、复盛元、天裕亨、丰盛魁、万盛兴、德和兴六大号,凭侍着雄厚的资本,投机倒把,大发横财。3年结账,每个身股都可分得红利2 000~3 000两银子。
当时一般的“六陈行”,每家平均约有骡马二三十匹,昼夜加工,成为人民食用品的主要来源。他们所用的粮食,除由本地粮店选进外,也从山西左卫(今左云)右卫(今右玉)及附近四乡采购。有时携带布匹、糖类与水烟、生烟赴后山一带进行“买树梢”和年对年的“期口交易”。
“六陈行”的“买树梢”与大斗进小斗出
所谓“买树梢”即是往年归化城附近与可可以力更(今武川县城所在地)等处的贫苦农民,每年春季因急于用钱,即向粮店、“六陈行”和当地富翁财主借支货物、现金,以所种的青苗庄稼作抵,议定极低的价格,到了秋收时,照议价交粮,这就叫做“买树梢”。所谓“期口交易”是指另有一些六陈行在春季或秋季,将各种货物,以极高的价格,赊给乡民,以一年为期限,到时彻底清账,这就叫做期口交易。
“六陈行”在出卖米面的时候,也是大斗进小斗出。进粮的时候,使用官斗,卖米的时候,改为26斤的栏柜斗,一买一卖,在数量上就有很大出入。日常所用的秤锤,也有的内注入铅质。入大出小,成了“六陈行”的剥削惯例。“日伪”时期,为了抵抗官税,防止特务汉奸的讹诈,每家都立有假账,予以蒙蔽。如遇凶年饥荒,“六陈行”便囤积居奇,借机大发横财。
“六陈行”的内部管理
当年归化城“六陈行”的内部组织,计有大二三掌柜分层负责,总理业务;银钱往来与粮食米面的进出,则由记账先生凭条登账;至于上街买卖与粮仓的检查保管,也指派柜伙专人担任;青年学徒(当时也叫住地方的),除了清扫柜房,奉侍掌柜,招待客人而外,每天还得赶上毛驴,将各家顾主所订的米面一一送到。
磨房与碾房的加工,即由磨官头儿与碾官头儿分别负责。磨房开磨后,终年昼夜两班轮换,每班加工的原料(如小米、莜麦)都以一石一斗为标准,若畜力不济,也可改为9斗。碾房开磨,也是夜以继日,平均每班可推谷子15石。他们的待遇,是雇佣性质。磨官、碾官每人每月仅得城钱3吊,头儿可得5吊。临时短工为5吊。辛亥革命后,工资上升,头儿可得白洋八九元,磨官、碾官为六七元或四五元。夜官以看守门户/管理骡马为专职,其工资最少,以前每个月仅得2吊,但他们在喂饮牲畜的时候,经常偷盗草料,也是一项公开的秘密。
归绥面行电动化的先导
民国18年(1929年),归绥一带大旱,粮食奇缺。新旧两城的六陈行缩减为110余家。那时,天津商人杨品山,为了增加产量,获取厚利,曾在小召前安装电动石磨,起名为德源面庄,为归绥面行电动化的先导。
归化城“六陈行”的碾米磨面工具,曾一直是以畜力带动的石磨、石碾。宣统时期每年加工面粉250万斤左右。民国23年(1934年),绥远电灯公司根据粮食丰收、粮价降低的情况,请准省府安装了钢磨5盘,附设面粉厂。当时日出面粉1 000袋,每袋49磅,年可出面八九百万斤。面粉以“五塔牌”为商标,行销时,分为三等;绿号为头等,每袋定价2元5角5分;红号为二等,每袋定价2元3角;蓝号为三等,每袋定价一元。北京、天津都设有代售处。后因炭费、运费不断增加,其营业额也受到很大影响。民国22年(1933年)前后,新旧两城的磨房共计70余家,年出面粉约100万斤左右。莜麦面的产量很大,荞面、豆面、炒面次之(豆面用小麦、豌豆混合磨成,炒面的原料为莜麦与黄豆)。电灯公司面粉厂所安装的钢磨,完全由外国进口。如有英国拨柏葛锅炉公司制造的锅炉,亨得来钢厂的引擎,德国亚美公司所造的洗麦机、净麦机、打麦机等。义合面粉厂也有德国禅臣洋行10马力的电动面粉机一台。抗战结束后,真光面粉厂,以“真光牌”为商标,规模较大,设备有西洋钢磨,日出面粉六七百袋。另外潘子良创办的裕盛永面粉厂,以永车牌为商标,安装电动石磨四盘,昼夜可加工小麦20石。当时,电灯公司面粉厂的职工、徒工,每天劳动时间为12个小时;义合、德源两面庄为10个小时;其他磨房的磨官,多以完成小麦一石一斗的加工为一天的劳动时间。
新旧两城“六陈行”的变迁
“日伪”时期,新旧两城的“六陈行”,计有70余户,其中安装电动石磨的字号10多家。电动化的粮食加工,在日寇掠夺面粉时,曾发展一时,但在粮食统制之后,原有的六陈行,因不堪压迫,大部分倒闭,苟延残喘,能维持现状者,仅存30余户。日寇投降后,新开张的面铺、碾房与原有的共计70余家。其中以广兴泰、德元号、王记、永和昌、丰盛魁、庆隆茂、意生号与绥远救济院面粉厂、新绥面粉厂的营业状况为最好。机制面粉厂,除电灯公司面粉厂外,尚有真光与裕盛涌两家。解放初期,又有五一面粉厂开设于南柴火市。不久,所有的面铺、碾房、缸房、油房都随着社会的发展,改变了生产关系,大部分都融合于粮食加工厂,开始了社会主义的经营方式。
“六陈行”著名掌柜孟维峻
归化城“六陈行”“复元永”面铺经理孟维峻,山西代州人。抗战结束以后,曾任米面业公会理事长。当时,因法币贬值,电灯公司不断提高电费,安装电动设备的面铺、碾房在孟维峻的领导下,将军粮加工费提高数倍,以示抗议,后经双方协商,各自酌减,才得到妥善的解决。解放军围攻绥远期间,绥远当局勒令各面铺、碾房送缴煤炭。通知公布后,孟维峻代表同业坚决反对,并指责当局,遂被撤职管押,后罚金元券4万元才将其释放。
1948年前后,晋绥区归绥货局局长牛翼,公开贪污、贿赂,向郊区缸房勒索黄金10两,后因金价贬值,又授意以洋布10匹代替。同时,又因永恒文缸房申请开业,借故处罚,此人种种不法行为,激起米面业公会的不满,遂由孟维峻带头提出控诉。太原区局调查后,将牛免职。
天义公掌柜兼福虎社总领王国珍
王国珍,山西崞县人。少年时期,因饥寒交迫来到塞外,投奔于归化城的天义公面庄。经过10多年的学徒与工作锻炼得精明老练,掌握了商人的经营之道。那时天义公以其资本雄厚,操纵市场。他担任掌柜之后,曾利用此便利条件迅速发展,被选为福虎社总领。
民国15~17年,晋军、奉军与西北军,为了争夺地盘,发生了内讧,地方负担更见加重。军用米面,多由福虎社主持摊派。这时,他又凭借职权,在“乱世好求财”的情况下,通过以少报多,将面折价等方法,得到一笔很大的收入。内战结束后,他就将这些不义之财先返原籍,委托复元永、万聚店代存生息,做起了高利贷勾当。很快万聚店的财东杨蒙公同掌柜王乎,借口赔累,将这笔巨款(约3 000多元白洋)骗去。虽经涉讼力争,也无完满结果。延至民国18年,王国珍的母亲服毒自尽以示威胁。肇事后,更以命案报衙,之后才由乡里调处,责成杨家出资厚葬,轰动一时。最后王杨两家家破人亡。
裕盛永面庄掌柜潘子良
潘立善,字子良,晋南荣河县人(今山西万荣县)。日寇投降后,他曾联合天主教神甫与教友赵贵等,筹资安装电动石磨4 盘,在庆凯桥开设了裕盛永面庄。所出的水车牌面粉,因粉质洁白,很受人们欢迎,致使五塔牌面粉的销路受到很大影响。那时,电灯公司董事会为了挽救面粉厂的营业衰落,曾借口线路与电费的纠葛,以暴力手段将裕盛永电线切断,以致生产停滞。为此,潘子良曾四处奔走,将事实经过与电灯公司刁难情况撰文,在《民国日报》与《绥闻晚报》发表,公诸社会,请求援助。经过几个月的纠缠,双方各持己见,矛盾愈加激化。当时天主教的势力已见衰落,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裕盛永又筹集了现金25 000元,购买到西洋发电机一部,自行发电,与电灯公司附设面粉厂展开营业竞争。但经过这一严重挫折,裕盛永受到很大的损失。延至1949年夏,太平召一带因洪水侵袭,酿成大灾,所存小麦,全被淹没,裕盛永也随之歇业。
“六陈行”米面价格的变化
民国18年(1929年),绥远各地大旱,当时的归绥市场,现大洋1元仅能买得白面5斤,莜面7斤。小米1斗,上涨到3.5元。外来的面粉,每袋飞涨为5.4元~5.8元。当时米面业的义记、王记、丰盛魁、三和兴等商号都趁机大发横财,获取厚利。
归绥沦陷初期,白面、莜麦面每斤均为伪币8分。后实行粮食统制,小麦禁运,坝口子、府兴营村、一间房与代州营子是当时的磨房集中地,所出的白面,多由一些面商(如段登昌等),串通伪警特务掩护入境,以高价行销黑市。那时,在市场上伪币1元,可买得白面7斤,莜面6斤。但往外贩运转售,即多半数以上的营利。官定的面粉价格,每袋为伪币6元上下,但多被汉奸特务套购占用,一般居民,只能以高粱面、混合面维持生活。
1942年以后,粮食统制更加严重,市内住户每家只准购存混合面22斤。这点粮食,人们连半饱都不够维持。当时,呼市的小召前,一天就饿死过20多人。1944年,伪币1元,仅能买高粱面6斤。那时主食奇缺,黑市猖狂,一些食品摊贩为了维持生意,有的以伪币1元仅能买到7两白面。抗战结束以后,法币1元,可买白面22斤、莜面25斤。后因金融紊乱,钞票贬值,粮食又一度飞涨。1949年春天,法币作废,银元券发行。白面1斤8分;莜面1斤7分,这样维持了几个月,直至新中国成立以后,归绥市的米面价格才走向稳定。
(作者:呼和浩特市团结小区东区03信箱)
- 年鉴刊物上一篇:(珍珠滩)读月亮(外三首)
- 年鉴刊物下一篇:(珍珠滩)凉城行
- 声明: 转载请注明来源于《内蒙古区情网》官方网站














 当前位置:
当前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