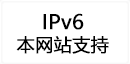第一期
- (卷首语)史志之歌
- (特载)关于表彰全国方志先进工作者、先进集体的决定
- (特载)关于表彰全国地方志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的决定
- (志鉴论坛)试论年鉴内容创新
- (志鉴论坛)修志确实也适文学笔法
- (志鉴论坛)志体与其它文体的比较
- (专稿)和林格尔县建国初民族工作概述
- (专稿)元代许衡的哲学思想
- (史海钩沉)马镫的发明与人物双狮纹金饰牌考
- (史海钩沉)乾隆三巡科尔沁草原
- (史海钩沉)话说康熙给噶尔丹嫁女
- (史料考辨)《斯文赫定在绥远》之辨误
- (文化长廊)蒙古族语言文字面面观
- (文化长廊)中蒙两国蒙古文图书馆学研究工作之比较
- (文物揽胜)京城明珠:什刹海
- (文化天地)大漠长河共沧桑──草原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历史贡献(连载八)
- (地方掌故)大盛魁与分庄小号—— “大盛魁现象”之八
- (民俗风情)呼和浩特地区民俗
- (方言丛谈)河套方言词汇特点
- (地名探源)内蒙古政区地名简述
- (人物)人物简介
- (珍珠滩)草原情思
- (珍珠滩)桂林杂记
- (珍珠滩)话说老通辽“八大家”
- (格言抄录)格言
- (文化天地)大漠长河共沧桑──草原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历史贡献(连载八)
- 发布时间:2011-05-14
- 来源:本站原创
八、满天星斗汇银河———草原文化对中华民族科学技术发展的贡献。
北方草原上的各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生长、生活在特殊的自然环境中,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并掌握了与这种草原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相适应的技术,在某些方面还上升为系统的理论,成为中华民族科学技术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畜牧业生产技术。
草原文化是与畜牧业经济联系在一起的。草原民族最先学会并掌握了捕获、驯养、放牧羊、牛、马、骆驼、鹿等牲畜的技术,并使畜牧业成为自身自存的最重要的经济基础。因此,“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既要熟知地理状况,根据不同地区的水草丰茂与否,选择放牧地,“随时畜牧”的游牧民族也要掌握天气的变化,根据风沙雨雪的状况,在自然灾害降临时做出必要的选择;游牧民族既要掌握不同畜种的牧养技术,以适应其不同的特点,也要根据牲畜在不同生产阶段、不同季节的特点,采取相应的牧养技术。这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已经形成了相当系统的技术体系,不少实用、适用的技术在今天仍然在畜牧业生产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其次,畜产品的加工技术。
牲畜既是草原民族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也是草原民族最基本的生活资料。但是,畜产品往往不可以直接作为消费品加以利用,而是必须经过必要的加工才能够用之于消费,因此产生了畜产品的加工技术。
由于季节不同,牲畜一般是“夏壮、秋肥、冬瘦、春死”———夏、秋季节水丰草茂,牲畜膘情最好,冬春季节牧草枯萎,乏草可食,牲畜普遍掉膘,甚至死亡。因此,入冬时是牲畜大量屠宰的季节。大量牛、羊肉要备作春、夏季的食品,就要制作成肉干储备。草原地区的风干肉,不能在阳光下曝晒,而应晾干或冻干,在清明节前10天左右取下放在坛子里,用数层麻纸将口子封严,40天后放开来,肉干鲜味如新,而且不变味,不长虫子,独具风味,令人食之不忘。
牛奶、羊奶、马奶、驼奶均具有丰富的营养,是草原民族保持健壮的体魄须臾不可缺少的饮料。但是,产奶的旺盛期也是集中在夏、秋季节,为了将此时食用不完的奶子留到冬、春季节食用,草原民族发明了乳品加工的技术,以发酵的方法制作酸奶,还可以用马奶、牛奶、驼奶制成醇香可口、营养丰富、滋补宜人的奶酒。在全世界的四大酒系中,白酒源于中国的中原地区,啤酒原产于古埃及、果酒以欧洲为代表,奶酒则是以蒙古高原为主要产地。更为普遍的,则是以牛奶制成奶皮子、奶豆腐及白奶油、黄奶油、酸奶油、黄油渣、酸酪蛋、甜酪蛋等奶食品。
草原民族的服装、靴鞋、毡房、马具等,大多是以皮革、毛皮为原料,其加工技术在草原民族的生产、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剥皮的时候,要精心细致,
避免破坏皮张,加工的时候要用木棰敲打,轻度发酵,认真刮削,反复揉磨。加工好的皮张,可以制服装、帽子、靴鞋、被褥、帐篷、铺垫等,还可以制作甲胄、箭囊、革囊、马鞍、缰绳、肚带等。牲畜的筋经过加工处理,可以捻成筋线,缝制服装、用品,用筋线制作的弓弦,因拉力大、弹力强而被人们称之为“良弓”。
草原地区野生动物较多,其皮毛极为珍贵,加工技术和制作工艺更为讲究。羊毛在草原地区用途极广,以制毡、制绳为主。制毛毡的技术性很强,需将洗净的羊毛加入适量的清水和粘着物,浸湿、加温、长时间的反复挤、压、擀、卷,使之成为需要的大、小、厚、薄不同的片状,再用来制作毡毯、毡靴、毡袜、毡帐等。
第三,交通技术。
蒙古草原是马的故乡。蒙古马是与野马血缘最近的品种。生活在蒙古草原的游牧民族是最早的马的主人,也是骑马技术最早的发明者。因此,草原民族被称之为“马背民族”。马具有灵活、快速、耐力强等优点,可以骑,可以驮物,可以拉车,以马作为主要的交通工具,不仅大大减少了人步行负重的劳累,加快了行进的速度,而且大大扩展了人的行动范围。在人类发明汽车、火车之前,在漫长的历史年代里马匹始终是陆上交通的主要工具之一。在蒙古高原中部、西南部戈壁地区和沙漠地区,则是以骆驼作为主要交通工具,并称之为“沙漠之舟”。
为了适应草原地区地域广阔、迁徙范围大的特点,草原民族掌握了就地取材制作车辆的技术。这种车辆轱辘较大,在坎坷不平、草高沙软的草原上行走便利,涉水渡河也如履平地。北魏时,敕勒人因乘这种轱辘高大的车辆而被称为“高车族”。蒙古族习惯用的勒勒车,也具有这种特点。车辆的制造,需要掌握较为复杂的技术,制造车辕、轴、轮等,需要坚硬又具有较好弹性的上等木材,按照适当的比例结构制作。针对平原地区、沙漠地区、丘陵山地等不同地貌,车辆的大小、形状也有明显的区别。
草原地区河流众多,不少河流河道游移,不适宜建固定的桥梁。草原民族发明了“束薪为桴”以渡水的办法。成吉思汗的祖先就曾以这种办法渡河。成吉思汗与王罕、札木合联军讨伐蔑尔乞部时,则是用猪鬃草捆成筏子度过了勤勒豁河。同时,草原民族也掌握了“跨河为梁,以便往来”的架桥技术。
草原民族的交通技术,不仅在自身的生产、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于扩大与中原地区的联系、促进东西方交流均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特别是元朝建立了贯通欧亚的交通网络体系,在交通建设与管理上,均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
第四,建筑技术。
草原民族被称为“毡帐之民”,是因为草原民族经过世世代代的探索,在实践中掌握了在草原地区就地取材制作毡房的特殊技术。现在牧区蒙古族的蒙古包,就是这一技术的结晶。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草原民族逐水草而居,过着迁徙不定的生活,这就需要住所必须搭建方便、易于搬迁;同时,草原地区冬季多暴风雪,春季多大风沙,又要求住所既轻便、又稳固;夏季气候炎热,还要求通风方便。蒙古包具备了上述要求。蒙古包是组合式的房屋,搭建、拆卸均很方便,用二、三辆勒勒车载运或用二、三峰骆驼驮运即可。蒙占包是圆形的,呈流线形,而且其架木结构十分合理,既能够紧密结合起来,又能够有效分担压力,抗风力强,搭建稳固的蒙古包可在十级大风中岿然不动。总之,蒙古包是草原建筑艺术的结晶。
阿拉坦汗将藏传佛教格鲁派引入蒙古草原后,逐渐建起了在草原上星罗棋布的黄教召庙,这些召庙大都兼具汉、藏建筑风格,具有很高的建筑艺术。至今在呼和浩特的席力图召、包头的美岱召、五当召等著名召庙,仍可感受到这类建筑的独特魅力。
第五,医学。
自古以来,草原民族即在实践中摸索走出一套适合当地特点的治疗疾病的方法。元代是医学大发展的时期,元世祖忽必烈设立了太医院,并在各地设立了惠民药局。元朝政府大力支持、提倡不同医学体系的交流,不仅草原医药与汉医药、藏医药广泛交流,还从中亚地区引进了“回回药物”,翻译刊印了《回回药方》,大大促进了医学的发展。
阿拉坦汗曾患足疾,三世达赖索南嘉措为之治愈。因此,伴随着藏传佛教在蒙古草原的传播,藏医药广泛流传,召庙均设有医学部,传授藏医、藏药,培养了许多喇嘛医生,并翻译、编写了不少的医学著作。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著名的藏医《四部医典》传入蒙古草原,对蒙医药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许多蒙医将传统的蒙医实践与藏医学结合,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提高,编印了不少蒙医著作,其代表作有:《蒙藏合璧医学》、《医学大全》、《脉诀》、《医学四部基本理论》、《药剂学》、《药五经》、《配药法》、《钊炙法》、《脉诊概要》、《外科正宗》等。汉医学的代表性著作《本草纲目》、《牛马经》等也翻译成蒙文。因此,蒙医学成为在草原民族传统治疗方法基础上,吸收汉医学、藏医学、回回医学理论与实践经验发展而成的系统的医学体系,成为中华医药文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六,历法与天文学。
季节变换对草原民族的生产与生活关系极大,草原民族也根据岁时变换的特点,总结出对气候变化的判断,“野草四月始青,六月始茂,至八月又枯”(《黑鞑事略笺证》,载《王国维遗书》第13册,第4页)。在历史上,蒙古人曾采用十二生肖纪年和干支纪年,后又袭用金朝的大明历。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郭守敬编制了《授时历》,经元世祖忽必烈下诏,颁行全国各地。《授时历》将回归年长度确定为365.2425日,是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时历。
蒙古族研究天文历法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民间将集天文、历法、星占、数学于一体的学问称之为“朱尔海”。人们运用朱尔海方法分析天文变化规律编制以60年为一个周期的历书,并且通过十分复杂的计算来推导日食、月食的时间。在重要的召庙中,一般都设有“时轮学部”(“洞阔尔学部”),研究天文、历法、星占学等。著名的蒙古族朱尔海家伊西巴勒珠尔就曾主持过时轮学部,并有《汉历概要》、《算学明鉴》、《随月计算新法》传世。
在清朝的国立研究机构钦天监中,蒙古族科学家居于重要位置。著名科学家明安图曾在钦天监工作50余年,历任五官正、监正。康熙、乾隆年间,明安图参加了《律历渊源》、《历象考成》、《历象考成后编》、《钦定仪象考成》等重要天文著作的编撰,编制、翻译蒙文《时宪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天文事业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蒙文《天文学》是一部重要的天文学著作,书中结合了当时的天文基础知识并吸收了西方天文学知识,对于研究蒙古族天文学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呼和浩特市五塔寺照壁上,有一幅石刻蒙文天文图。这幅图名为“钦天监绘制天文图”,以北极为中心,呈放射状,以阴文单线刻出黄道圈与赤道刻度圈,标明了三垣二十八宿,是蒙古族天文学家的杰作,反映了当时蒙古族天文学的发展水平。
应当指出,由于自然、社会诸方面的原因,草原地区的科学技术发展在许多方面落后于中原地区。但是,草原民族对中华民族科学技术发展的贡献仍然是不容忽视的。
综上所述,自古以来,草原文化在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中华文明的演进起到了重要的历史贡献。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和阐述草原文化对中华文明历史发展的重要贡献,非本文所可胜任。全面研究草原文化,准确阐释草原文化,努力弘扬草原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与时俱进,推进草原文化的发展,使之为将我国建设成文明、强盛的现代化强国充分发挥作用,是今天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和文化工作者共同的历史使命。(全文完)
(作者:内蒙古社会科学院)
- 年鉴刊物上一篇:(专稿)元代许衡的哲学思想
- 年鉴刊物下一篇:(专稿)和林格尔县建国初民族工作概述
- 声明: 转载请注明来源于《内蒙古区情网》官方网站














 当前位置:
当前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