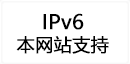第六期
- 【导读】本期导读
- 【志鉴论坛】浅论外文资料在编修新方志中的重要作用
- 【志鉴论坛】新民俗形态、成因和引导开发路径漫谈——以江苏省张家港市沙上片区为例
- 【志鉴论坛】浅谈第二轮志书资料的整体优化
- 【志书评议】一部堪称名品的新编区志——品读《宁波市海曙区志》丛谈
- 【志书评议】特色鲜明 亮点纷呈——《厦门市集美区志》读后
- 【工作研究】浅谈军事志的管理与利用
- 【史海钩沉】沟通内地与西北贸易的草原丝路——丝茶驼道
- 【史海钩沉】话说沃野设治局
- 【史海钩沉】内蒙古质量技术监督机构演变
- 【地名文化】吴坝名称考
- 【地名文化】太仆寺右翼牧厂与黑城子示范区
- 【文物鉴赏】居延地区动物纹铜饰件鉴赏
- 【盟市园地】吴俊升是张作霖副官吗?——与雷明义先生商榷
- 【盟市园地】张作霖与通辽
- 【盟市园地】1900年,中东铁路西线的枪声
- 【历史一页】锡林浩特四建英烈纪念碑
- 【大事记】内蒙古大事记(2014年10月21日—12月20日)
- 【珍珠滩】“英雄悲歌”与“英雄壮歌”之地——踏访大渡河安顺场
- 【珍珠滩】不是花时肯独来
- 【珍珠滩】沁园春·游眼镜湖
- 【志鉴动态】《内蒙古自治区志·文史研究馆志》(稿)评审会召开
- 【志鉴动态】《内蒙古自治区志·民俗志》出版发行
- 【志鉴动态】《地震志》(稿)评审会召开
- 【志鉴动态】《商都县志(2005~2013年)》(稿)评审会召开
- 【志鉴动态】全区盟市地方志工作机构主任现场观摩工作会议召开
- 【志鉴动态】《方志内蒙古·通辽篇》完成拍摄任务
- 【志鉴动态】《发展和改革志》出版发行
- 【志鉴动态】《方志内蒙古·锡林郭勒篇》拍摄告竣
- 【志鉴动态】蒙古文版《兴安盟志》出版发行
- 【志鉴动态】《红十字会志》篇目讨论会召开
- 【史海钩沉】沟通内地与西北贸易的草原丝路——丝茶驼道
- 发布时间:2015-03-08
- 来源:本站原创
早在辽代,北方草原上已经存有“丝茶驼路”,它是在辽代大唐通西域的基础上,随着辽朝对北方各民族的统一以及与东西方友好往来而开拓出来的以上京为中心联络西域以及东方高丽、日本等国的 “草原丝绸之路”。随后在明清两代,漠南蒙古各部又进一步加大了与西北及喀尔喀蒙古、俄罗斯的友好往来,开通了与新疆及中亚国家、外蒙古、俄罗斯等地区和国家的贸易之路,被史学界称之为“草原丝绸之路”。
除此,还有一条并未引起人们足够地注意和重视的草原丝路,那就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北部边陲重镇归化城 (今呼和浩特)、张家口等地,向西北延伸,以沙漠之舟——骆驼为主要运输工具,由驼工们开拓出的通往新疆、外蒙古、俄罗斯的商路,由于运输的货物主要是绸缎、布匹和茶叶等物,所以,内蒙古史学界将此条草原丝路定名为“丝茶驼道”。
“丝茶驼路”的拓展及经济往来,对沟通中原地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西北边陲的政治经济、巩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部边防、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促进中国对外贸易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本文就清代至民国时期呼和浩特地区驼商开辟的丝茶驼道贸易及历史作用做一概述。
一、草原丝茶驼道的形成、发展及走向
16世纪中叶,俺答汗统领土默特部驻牧丰州滩,统一漠南蒙古各部后,中国北方出现了相对和平稳定的局面,蒙古草原畜牧业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迫切需求发展与中原地区的贸易关系,以满足牧民的生产、生活需要。俺答汗顺应民意,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终于于明廷达成互市共识,进而实现了历史上著名的“隆庆和议”“俺答封贡”。“封贡”的实现,对于促进土默特万户以及右翼三万户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从此,归化城成为了明蒙互市中蒙汉贸易的重要集市及晋、陕、蒙、新商业贸易的中介。当时明王朝规定,中原商贾不许深入蒙古腹地贸易,于是每年漠南、漠北、漠西蒙古贵族就自领大批驼队来到归化城购买他们所需的生活用品,同时也出售带来的蒙地畜产品。这样,来往于蒙古腹地和归化城之间,就逐步出现了几条或长或短,断断续续的驼运栈道,这便是草原“丝茶驼路”的雏型。
清朝初年,在归化城的清军队伍里,出现了一种为清军在外地提供军需服务的随军经商的商人。康熙中叶,康熙帝率大军亲征准噶尔部噶尔丹(在今新疆西部)叛乱的时候,由于战线拉长,清政府的随军贸易做的就更为庞大。随军商贾除为部队贩运军稂、马匹等军需外,同时还兼做当地的民间生意;他们把从中原地区购买的茶叶、布匹、粮食以及草原牧民所需的生活日用品运往草原,而换回草原牧民的牲畜、皮毛等畜产品之类。人们即把这些随军流动经商的商贾称作“旅蒙商”,当时“旅蒙商”的流动经商活动主要以骆驼为运输工具,一般都是沿历史上的古驿站栈道和明代蒙古腹地盟旗来归化城易货的驼路逐水草而开拓前进,足迹遍布漠南、漠北、漠西广大草原。所以草原“丝茶驼路”的最初开拓阶段应在明万历九年(1581年)归化城已初具规模,作为南北货物的集散地起,到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清政府第一次平定噶尔丹叛乱的时候。
康熙三十年,清政府召集漠北喀尔喀三部和漠南内蒙古四十九旗的王公贵族在多伦诺尔会盟时,蒙古王公一致向康熙帝上书,请求政府派遣更多旅蒙商贾深入蒙古地区进行贸易。康熙帝应允了他们的请求,但考虑到当时北方的威胁还没有完全消除,所以清政府对旅蒙的商人设定了严格的限制。规定凡是去内外蒙古和漠西厄鲁特蒙古的商人,必须得到特定衙门的批准,从规定的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等指定的关口进入到指定的蒙古地区进行贸易,不准前往未经指定的地区经商。当时在蒙古地区的贸易区主要划为前、后、西三个营地。旅蒙的商队出关时,必须在经商许可证上注明商队人数、货物品种、数量以及起程和返程的日期等诸多内容,到达蒙古地区后,也必须要在当地官吏的监督下进行贸易。清政府尽管对旅蒙商人给以种种限制,但毕竟入蒙地经商,已成合法化,所以中原商人,特别是山西、直隶等地商人蜂涌而至。于是,内地通过长城沿边道口,循着中原通往蒙古地区的驿道,由近及远,逐渐深入漠北的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及至更远的唐努乌梁海,以及漠西的古城、迪化、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的厄鲁特蒙古地区。这样,通往漠南、漠北、漠西的驼道逐渐拓展、疏通、延长。
乾隆中期以后,清政府对蒙地“封禁”政策和对旅蒙商入蒙地的限制进一步松弛,遂使蒙古地区的商业贸易日趋兴旺,旅蒙商贾在蒙古地区开始设立永久性的商号。特别是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军平定青海、新疆占领伊犁后,旅蒙商人开辟了一条由前营到后营到西营的“营路”,于是,归化和内地到土默特以及走外路(库伦)与西路(哈密)做蒙古生意的汉族商人及庄铺买卖字号,都争先恐后到归化城及北部草原地区发展,因而,归化城成了旅蒙商贸易的主要基地,“起初繁荣时期,每年输入70—80万只羊、3万匹马、1万头骆驼和牛;输入五六百万两的皮革、毛绒;而由新疆伊犁一带运来的货物也达到一二百万两。”①
清乾隆中期以后,由于草原“丝茶驼路”上的经贸活动进入繁荣阶段,“丝茶驼路”站段固定,线路畅通,遂成为我国中原内地与西北蒙地以及中亚、沙俄商贸的最大经济命脉。据《蒙古与蒙古人》一书记载,光绪初年归化城每年的茶叶输出量为10余万箱,主要是砖茶。其中24块一箱者主要供应土默特地区的蒙汉民众,每年销售4万箱;39块一箱者主要运往乌里雅苏台,每年约3万箱;运往古城的主要是72块或110块一箱的砖茶,木墩茶和白毫茶(红、绿茶)主要则销往伊犁和东土耳其斯坦以及俄国的维尔年斯克、塔什干、鄂木斯克、托木斯克等地,每年销量3—3.5万箱。 当时归化城成为贸易经营的重要基地,贯通了中原内地与漠西、漠北草原,以及中俄边境的贸易交流,形成了蒙古地区一个自成体系的庞大商业网。归化城的旅蒙商把从全国各地贩运来的货物,经归化城运往西北边陲及外蒙古各地销售;再把从外蒙古及西北各省贩运回来的牲畜及畜产品,经归化城转售内地。因此,归化城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适于蒙古地区生产、生活需求的商品,为旅蒙商贸易提供了充足的货源和商品转运的便利条件,更加密切了内地与西北边远地区的经济联系,充分发挥了商品贸易中转基地的作用。
自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被迫与之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帝国主义列强凭借这些不平等条约攫取了许多商业特权,使奔走于草原“丝茶驼路”上的旅蒙商人在贸易成本上处于劣势地位,民族商贸受到严重冲击。进入20世纪初,随着西伯利亚铁路、中东铁路以及京张铁路、京绥铁路的通车,使俄国把对华贸易的中心由蒙古转移到东北。俄商还利用享有的通商特权,直接深入中国内地进行贸易,这种状况使旅蒙商人在对俄贸易中的中介作用丧失殆尽,也导致了归化城、张家口、库伦、恰克图等传统边贸中心日趋没落。辛亥革命后,由于国内军阀混战,局势动荡,再加上外蒙古在沙俄支持下宣布独立,没收了旅蒙商在外蒙古的资产,使旅蒙商遭受了重创,遭此变故归绥最大的旅蒙商号大盛魁也于民国十八年关闭歇业。1929年以后经常往来于草原“丝茶驼路”,承担与西北贸易的商人是归绥的回族驼户,当时这些驼户有骆驼五千多峰,每年营业额约30万银元。及至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后,日本侵略者对华实行了强制的经济统制,归绥的日本人对驼户的外出经商规定了若干限制。其中规定,凡出境(出日占领区)商贸,必须经“贸易通商会”的审查,即使得到许可,也要派人跟随驼队监督贸易。加之当时统治新疆的军阀盛世才实行全面封锁政策,出入新疆的贸易皆被封死。从此草原“丝茶驼路”开始衰败。抗战胜利后,通往新疆的驼道又重新开放,归绥和包头的驼商又开辟了新的驼道,继续与西北边陲进行着贸易,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前。
清代至民国时期以归化城为起始点,通往漠北、漠西的草原丝茶驼道各有三条。每条线路上的站段,虽在这几百年中时有变迁,但整条线路走向变化均不大。
通往漠北的三条驼路为:
前营路:归化城——可可以力更(武川)——召河——乌里雅苏台(前营,今蒙古国扎希哈朗特),线路共经60站,全程约5320—5630里。
后营路:归化城——可可以力更——召河,沿前营路行54站至格里塔拉分道,向西行110里到川镜,经察汗哀勒更——科布多(后营,今蒙古国吉尔格朗图),线路计73站,全程约6620里。
库伦路:归化城——可可以力更——召河——济斯洪果尔(从此站进入蒙古国)——库伦(今乌兰巴托),计39站,全程约2870里。
库伦路实际有三条,但这条路最捷近,而且途中多天然河流、水泉、水淖,同时每隔数十里就有人工开凿的井,故驼队多行此道。
库伦路的另一条叫“信杆路”。此路由归绥出发,经可可以力更、乌兰花(四子王旗)、二连,然后进入外蒙古,沿着电线杆而行,这样方向不会迷误,而且一路水草丰美,路亦平坦。
库伦路还有一条叫“大西路”,此路由归绥出发,沿前后营路向北行至外蒙古的岱青贝子,再转向东北行至库伦。
库伦路的后两条路多有逾绕,所以走这两条路的驼队较少。
前营路、后营路、库伦路从1924年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即关闭。呼和浩特的驼运就只有走大西北去新疆的古城子路。古城子路实际上有三条,即大西路、小西路、新辟路。
大西路:归绥(今呼和浩特)——可可以力更——召河——百灵庙——老爷庙(从此站进入新疆地界)——木炭窑子——卧龙驹口——只几湖——古城子(新疆奇台县),计72站,全程约5430里。
小西路:归绥——可可以力更——召河——百灵庙——什拉哈达(从此站进入外蒙古地界)——至哈拉纽独(与大西路线合并)——古城子,线路计72站,全程约5470里。
大西路、小西路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一直是内地进入新疆的驼运通道;它基本上是沿着内、外蒙古边界行走,时而在内蒙古,时而在外蒙古。1924年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封锁了边境,内地驼队就不能再进入外蒙古行走,所以驼工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在旧路之南沿边境中国一侧,另辟出一条新路。这条路走内蒙古的达尔罕旗、茂明安旗、乌拉特旗,然后入宁夏、甘肃、最后进入新疆。这条路主要是由归化城的回族驼工开拓出来的,路途上虽然水草不佳、流沙拥阻、地匪经常出没,但其为沟通内地与西北的商贸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
新辟路:归绥——可可以力更——召河——百灵庙——察哈点勒素——拐子湖脑包泉——芦草井子(从此到下站称“连四旱”,计350里,即走四程路都没水)——野马井子(从此到下站称“连三旱”,路程为310里)——骆驼泉——只几湖——古城子,线路全程约7660里,计有74站。
1931年以后,由于匪患众多,驼商行至二里子河即绕向西南斜行十五、六站,至肃州星星峡,出星星峡进入新疆境内,再向西北行十二站,至哈密;由哈密再行十二站,到达古城子。
草原丝茶驼道并非至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库伦、古城子止。如库伦路就从库伦向北出境到俄国恰克图,然后沿贝加尔湖再深入到西伯利亚腹地。而古城子路,从古城子向西行到迪化(今乌鲁木齐),再向西至伊犁,西北至塔尔巴哈台,分别进入俄罗斯境内。据说大盛魁在鼎盛时期,驼队曾到达俄国的京城毛斯坛瓦(今莫斯科)。故古城子路将内地、呼和浩特和中亚地区沟通了起来。
草原“丝茶驼路”上的站段,因水草、地理条件不同而有长有短,长者一百三四十里,短者五六十里。其中有的站点有水草、河淖或人工水井,可供驼工使用;而有的站却是荒漠一片、水草全无,最多时走三四个站点都没有水可用。凡遇这种站点,在未到此站之前,人驼必须装好足够的淡水。
二、草原丝茶驼道的贸易及货币
清代及民国时期,随着草原丝茶驼道的畅通,从事商业活动的各类商铺遍布阴山南北及草原地带。据不全统计,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60年代,仅漠北地区定居的旅蒙商号多达500余家,经商活动的商人多达20余万。他们在库伦、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建筑了许多宽敞的店铺、货栈,形成了蒙汉等族进行贸易交换的“买卖城”。当时产于湖北、安徽、福建的砖茶,产于河南、江西、山东的布匹、生烟、陶器、瓷器,产于河北、山西、陕西的麦粉、金属器皿、供佛用品,产于江浙、两广的绸缎、蔗糖,源源不断集中到归化城、张家口等地,然后再由草原“丝茶驼路”运往漠南、漠北、漠西草原。
商队从归化城起程时,所运货物有砖茶、米性茶(红茶末)、布匹、绸缎、生烟、麦粉、蔗糖、调味品、陶器、瓷器、金属器皿、佛事用品、小百货、日杂用品及家具。从新疆、俄罗斯等地和国家回程时,所运货物有老羊皮、羔皮、细猎皮、羊毛、驼毛等皮毛,毛呢,甘草、枸杞、黄芪、贝母、灵羊角、鹿茸等药材,玉石,葡萄干等干果,金属用品等。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金融业的繁荣,货币的需求量和流通量大大增加,呈现出新旧交替、中外混杂的局面。但蒙古地区由于受牧业经济基础、地域环境、交通条件等方面的限制,金属货币往往不能适应商品交易的需要。因此,其商业贸易,还主要是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换关系,形成了草原牧区以土布、砖茶、绵羊等作为交换媒介的特殊货币形式,同时,也流通有各种货币。
(一)特殊货币
这一时期旅蒙商人采取南买北卖、北买南卖的形式,即从张家口、天津、北京、上海等地贩上土布、花缎、丝绸、茶叶、瓷器及药品等物,运到西北各省及库伦、科布多、乌里雅苏台、恰克图等地销售;再从销售地收上灰鼠、扫雪、旱獭、北极狐、狼、貂等皮张、皮革制品及贵重药材,如鹿茸、贝母、枸杞、麝香等物,运销内地各省。
土布在当时是十分重要的交换媒介,旅蒙商人在恰克图的贸往来都是用土布来作价的。据张诚《鞑靼旅行记》记载,1688年,法国传教士曾如此描绘他们和蒙古人之间的以货易货:“在路上,我们碰见几位喀尔喀鞑靼人。他们携带着骆驼、马匹和羊出售或进行交换。我们用茶叶和烟草与之交易,价格约为十五索尔可换一只羊……用他们的牲畜交换布、烟草及茶叶……他们不愿收钱,而只需布……拒绝收钱,但要布、茶叶、烟草和食盐作补偿”。
《绥远通志稿》记载,清代归化城在以货易货中,主要用绵羊和砖茶作为交换媒介。砖茶与绵羊的比价是每只绵羊相当于7块三九砖茶(三九砖茶指每箱包装39块,每块约值白银三钱左右)的价值,每只好绵羊可达12块三九砖茶。《蒙古地志》载恰克图砖茶市情:“凡市场商店购买物件,有以小片砖茶标价者,土人亦喜相接受,如碎切之银两。大抵一头羊换砖茶十二至十五个,骆驼可换百二十个至百五十个。”
砖茶与羊皮的比价是每张绵羊皮约相当于1.4块三九砖茶;与羊肉的比价是每块砖茶相当于3斤绵羊肉;与羊毛的比价是每块三九砖茶相当于2.5斤绵羊毛。砖茶与马的比价是每匹普通马相当于46块三九砖茶,每匹好马可达86块三九砖茶。
归化城的绵羊和砖茶比价在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地有明显的物价差距。土布、绵羊和砖茶是在丝茶驼道以货易货中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
(二)金属货币
由于草原丝茶驼道商业日趋兴旺发达,旅蒙商队把银两、银元、铜钱、铜元相继带入驼道,同时也使许多外国钱币流通到驼道上,成为丝茶驼道上流通货币的一部分。
在清代以前的草原丝路上,已有货币流通,以银两和铜钱为主,入清后,仍流通银两和铜钱。从清代晚期开始出现了银元、铜元,与银两和铜钱混合流通于草原丝茶驼道上。
1.银币
在清代白银和铜钱都可无限制使用,货币本位银、钱平行。交易额大用银,小则用铜钱,归化城及草原斯茶驼道上用银两多于铜钱。银币分银锭和银元两种,常见有山西省清代和民国初年的大小元宝,如“大同元宝”和“太谷宝”等,也有“归化元宝”。由于各种元宝的重量和质量各不相同,使用非常不便,而全国各地的衡器千差万别、标准不一,故称银时,归化城一般用城钱平,城钱平一两相当于山西祁县祁公平的一两一分八厘二毫、相当于汉口汉沽平的一两三分四厘六毫、相当于上海规元的一两九分二厘九毫、相当于天津行平的一两三分六毫。银元1元相当于城钱平的六钱五分四厘七毫二,也有以库平银、湘平银为标准的。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国民党政府在全国推行废两改元,以银元为货币单位,白银才退出流通领域。清政府光绪年间发行了银元,归化城在光绪末年才始流入,与铜钱的折合率为每800枚铜钱兑银元1元。民国三年(1914年)后,中国银行相继在归绥、包头设立分支机构,大量银元流入草原丝茶驼道,常见有袁大头、孙中山小人头、英国站洋、墨西哥鹰洋、航船、俄国羌人头等,还有日本、美国贸易银元,但流通量不大。
2.铜钱
草原丝茶驼道上流通的铜钱,以清政府或各省官钱局铸的为多,间杂有前朝铜钱,大小不等,成色不一,品种繁多,非常混乱。品种有样钱、制钱、黄钱、白钱、青钱、红钱、普尔钱等。由于钱的比价不断涨落,时有变化,而一些公私铸铜钱出现了减重或劣质品,如沙壳、风皮、鱼眼、砂板、鹅眼、水浮钱等。为此归化城有些钱商在钱市上大搞投机活动,直到民国十二年(1923年)政府限制后才停止。清初,归化城是以96文抵100使用,乾隆、光绪时期以86文抵100使用,光绪末年则又降为80抵100,此间各地钱法也有所不同,如毕克齐光绪末年是68文抵100使用。
从草原丝茶驼道的必经之地可镇(武川)出土的两批清代窖藏钱币来看,最晚的是宣统元宝,最早有汉五铢、半两钱,以清钱为主,其次是北宋钱,不见民国铜元。可见这两批窖藏铜钱沉淀于清末,是民国初年铜元上市,铜钱逐渐停止使用时沉淀下来的。从此也可反映出丝茶驼道贸易货币铜钱的流通是以清钱为主,不分朝代一律通用。
3.铜元
铜元民间俗称“铜板”、“铜子儿”,为清末铸造,分红铜和黄铜两种。每枚重一钱六分的铜元当制钱10文,与银元比价为100:1;重三钱二分的铜元当制钱20文,多为清政府及各省铸造。清末民国初年流通于草原丝茶驼道的铜元,常见有山西铜元局所铸的红铜元,另有“光绪元宝”和“大清铜币”等种类。
(三)纸币
纸币也有两种,一种是地方官银号或银行发行的兑换券;一种是商会或商行发行的帖子。归化城及草原丝茶驼道上流通纸币有以下几种。
大清银行纸币:面额为100元、10元、5元、1元数种。
俄国国立银行兑换券(羌帖),面额分500留、100留、50留、25留、10留、5留、 3留、1留几种,日俄战争后禁止流通。
民国时期还有许多地方票券流通于草原丝茶驼道上。
平市票:绥远平市官钱局在民国九年发行了5吊、1吊、500文、300文、100文五种制钱票及面额为1元、5元、10元、1角、2角、5角的银元主辅币兑换券和面额为10枚、20枚、30枚、50枚、100枚铜元券;民国二十年改发新票,旧票折半兑换,民国二十二年又四折兑现。抗战爆发后停止使用,被蒙疆银行票收兑。
晋钞:1919年山西省银行发行,有银元和铜元兑换券两种。由于旅蒙商人中多为山西籍人,故晋钞发行后很快流通到驼道上。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改组山西省银行后,以新钞1元兑旧钞20元收回,使旅蒙商人遭受巨大损失。
西北银行票:由冯玉祥创办的西北军随军银行,民国十四年(1925年)在归绥和包头设分行,大量发行纸币。初发时还可与中国银行票、交通银行票等价流通,西北军撤退时西北银行撤销,票券停兑成为废纸。
丰业票:丰业银行是归绥市以商股集资开办的商业银行,民国十九年(1930年)成立后,发行了面额为10元、5元、1元的以银元为本位货币的流通券。两年后贬值50%,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又发行新票及1角辅币,日军侵占归绥后被蒙疆银行票取代。
绥西垦业银号票: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由太原晋绥公署创办,面额有10元、5元、1元、2角、1角五种,共发100万屯垦券,1936年并归山西省银行后,仍有66万元未收回成为废纸。
蒙疆票:日军侵占华北后,于1937年11月23日宣布成立伪蒙疆银行。1938年3至5月陆续发行了面额为100元(三种)、10元、5元、1元纸币及5角、1角、5分铜质硬币和1分、5厘铜质硬币,1940年又发行了5分、1角、5角纸币,还把日本铸的10钱、1钱铝币投入市场流通。抗日战争结束后,蒙疆票由绥远省银行以法币1元换4角收兑。
党中央银行券及法币:党中央银行券是民国十七年(1928年)11月1日由国民党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规定中国银行、农民银行、交通银行和党中央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并负责收兑其他各银行的各种票券。从1942年4月1日起,法币由党中央银行统一发行,日本投降后流通于内蒙古西部地区。由于发行量增大,贬值到论捆不点数,遂于1948年8月停止流通,以金元券1元收兑法币300元。金元券发行不到1个月开始贬值,到1949年6月25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规定金元券5亿元兑银元1元,以至城市交易又改用银元和布匹作为媒介,退到了以货易货的原始状态。国民党中央银行于1942年4月还发行过一种“关金券”,每元关金券兑法币20元,日军投降后开始在内蒙古西部地区流通,后被金元券取代。
银元券:1949年6月绥远省银行发行,主币面额1元,辅币有5角、2角、1角、5分,铜质硬币有5分和1分,1元主币与银元等价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人民币收兑。
帖子:内蒙古西部地区流通于驼道的票据,主要是大盛魁票庄印制的,上印有金额、发行商铺名、号码、发行年、月、日,并盖有商务会的印章。这种钱帖有的以清朝制钱为标准,面额大的当35吊文,小的当1吊文;有的以小洋钱为标准,面额大的有当50角,小的当1角。得到商会担保和官方认可的发行者,其发行数量一般不超过固定资本的一半,如支付发生困难,要把全部财产委托商务会,由商务会支付。否则,要受到法律追究,其财产仍由商务会清理变卖后,支付钱帖持有者。
上述流通的诸多钱币,虽然其制造与发行并非专为草原丝茶驼道贸易使用,但确实流通到了归绥地区的草原丝茶驼道上,其中不能排除部分货币参与或充当了丝茶驼道贸易货币。由于政治和军事原因,各官私银行发行大量纸币,使草原丝茶驼道贸易货币丰富多彩,同时也造成了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这也是大批旅蒙商人在民国年间纷纷倒闭的一个重要原因。草原丝茶驼道上大量外币的流入,给蒙汉各族人民带来了灾难,也反映出了外国列强对中国赤裸裸的经济掠夺。
三、草原丝茶驼道贸易的历史作用
从清代到民国年间,一直活跃于内地与外蒙古及西北各省商道上的中外商旅,利用独特的交通工具——骆驼,进行长途贸易和贩运,这种独具地域特色和民族特点的商业活动,其历史作用是巨大的。
首先,草原丝茶驼道对城镇的兴起和繁荣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草原丝茶驼道的开拓促进了明代以来蒙汉互市据点的发展,一批新的草原城镇伴随着旅蒙商人的到来而兴起,尤其是作为驿路要冲的归化城、包头城开始成为繁盛的商业城市。特别是内地汉人的涌入,使中原农耕经济文化传播和渗透到大青山后及广大草原地带,刺激了草原牧民畜牧业、狩猎业的发展,并且为畜产品提供了广阔稳定的市场,同时也促进了草原城镇手工业、运输业的发展。
其次,加强了蒙汉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增强了各民族间的友谊。由于民族贸易往来的密切,加强了中原与北方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出现了民族迁徙、融合,使阴山南北形成了汉族为多数的多民族聚居区,其生产和生活方式既有浓郁的草原文化气息,又带着中原农耕文化的鲜明印记;随着时间推移,蒙汉民族间的交往日益密切,两种文化相互影响、融合,最终形成了新的文化特质。
再次,巩固和发展了中国的北方,维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一,捍卫了西北边陲。在草原丝茶驼路沿线,居住着蒙、藏、回、畏兀儿等众多民族,在进行商贸往来中,既繁荣了民族地区的畜牧业经济,拉动了当地运输业和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改善了牧民生活,又促进了与中原商品经济和道路交通的发展,增进了各族人民的团结,起到了巩固西北边防、维护边疆完整,促进边疆和内地经济互补及发展的作用。同时,丝茶驼路的边境贸易还沟通了中国和中亚地区的经贸活动,使中国的商贸活动延伸到了俄罗斯,进而拓展到东欧国家,加强了我国同中亚地区、俄罗斯及东欧等国的经济、文化、政治诸方面的交往。
总之,这一横跨亚欧经济交流的草原“丝茶驼路”,所起的作用完全可与“丝绸之路”、“海运之路”相媲美,实际上它就是丝绸之路在广阔草原上的延伸,所以它在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地位应引起国人的高度重视,也应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
注释:
①《蒙古族通史》(修订版)下第144页,民族出版社,2001年。
(作者:内蒙古自治区钱币学会秘书处)
- 年鉴刊物上一篇:【大事记】内蒙古大事记(2014年10月21日—12月20日)
- 年鉴刊物下一篇:【历史一页】锡林浩特四建英烈纪念碑
- 声明: 转载请注明来源于《内蒙古区情网》官方网站














 当前位置:
当前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