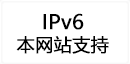第三期
- 【导读】本期导读
- 【志鉴论坛】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创新之我见
- 【志鉴论坛】二轮志书对老城区改造的记述
- 【志鉴论坛】地方志工作法制化探究
- 【专稿】元帅行吟内蒙古
- 【专稿】侯一民:设计人民币的蒙古族画家
- 【专稿】王铎与内蒙古网球运动
- 【学术探讨】达斡尔族村名的文化内涵
- 【史海钩沉】皇帝下台修成佛学大师
- 【史海钩沉】清代归化城土默特两翼军事建制及其演变
- 【史海钩沉】博尔本察——走出济沁河流域的鄂温克民族英雄
- 【史海钩沉】轰动一时的凌升事件
- 【人物剪影】丹青春秋 洇润驼乡
- 【史海钩沉】直属机关“大学校”成立前后
- 【志坛撷英】志坛宏篇——陈曼平方家学术思想研究兼评新著《漫漫集》
- 【大事记】内蒙古大事记(2013年4月21日~6月20日)
- 【珍珠滩】满江红·修志有感(外一首)
- 【珍珠滩】七绝·田园诗七首
- 【珍珠滩】圣水梁野游杂咏
- 【书画摄影】李世嵘国画作品
- 【书画摄影】包巴特尔摄影作品
- 【志鉴动态】全区地方志机构主任会议在恩格贝召开
- 【志鉴动态】自治区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杨泽荣一行赴陕西省考察学习
- 【志鉴动态】自治区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杨泽荣一行赴京津学习交流
- 【志鉴动态】东部区《水利志》启动及志书编纂培训会议召开
- 【史海钩沉】轰动一时的凌升事件
- 发布时间:2014-01-02
- 来源:本站原创
-
日本关东军一手炮制“满洲国”后,相继颁布《治安警察法》、《暂行惩治叛徒法》等一系列反动法令,给日本军警以“临阵格杀”的生杀大权,使之可以随时逮捕与擅杀抗日人员甚至无辜群众。对于少数民族中充当伪官吏的上层人物,如稍有不满或发表不同意见,亦在其迫害与残杀之列。1936年4月发生的凌升事件即是一例。这一事件震动了当时伪满统治机构的上层,亦对以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凌升,达斡尔族,生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原索伦右翼正黄旗(今内蒙古鄂温克旗)人。其先祖明信阿于嘉庆八年(1803)奉命从戎,由布特哈地区到呼伦贝尔,任厄鲁特旗总管;其父贵福,亦任厄鲁特旗总管、呼伦贝尔副都统。凌升幼年随父学习满文,稍长入呼伦贝尔官立初、高级小学学习汉文,后又入呼伦贝尔蒙旗中学。
凌升由呼伦贝尔蒙旗中学毕业后,先后任管理台站笔帖式(秘书)、骁骑校、劝学员、呼伦贝尔自治会副会长、海拉尔警察局副局长等职。此时,正值清末民国初年,清廷在这一地区改设“民治”,废副都统衙门,“移民实边”。由于这一“改革”在实施过程中过急,又侵犯了少数民族的利益,激起少数民族官员和牧民的普遍反感。他们在厄鲁特旗总管胜福、新巴尔虎右翼总管车和札的带领下,于1912午1月发起呼伦贝尔历史上的第一次“独立”。在这次“独立”中,凌升作为胜福的得力幕僚,初露锋芒。此后,他被提升为佐领兼呼伦贝尔副都统署左右两厅帮办。
1917年夏,在日本扶助下,巴布扎布残部色布精额匪帮2000余人突然袭击并占领呼伦城。在这紧急时刻,受副都统胜福的委托,凌升组织蒙旗联军,讨伐色布精额匪帮。在这一事件中,又一次显示了他出众的组织和指挥才能,深得副都统胜福和各蒙旗的信任。不久,他出任厄鲁特旗总管、署理索伦右翼总管等职。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外蒙古”的“自治”失去依靠。在这种情况下,凌升等人顺应潮流,于1920年1月6日呈请东北当局并转请党中央政府,取消“特别区域”,废除1915年签订的《中俄会订呼伦贝尔条件》。同年2月,呼伦贝尔地区恢复“民治”,设善后督办公署,同时,仍保留副都统署,专辖蒙旗事务。由于凌升的卓越才干和突出的政绩,使他逐渐成为呼伦贝尔地区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重要代表,亦引起有关方面对他的重视。《呼伦贝尔志略》称他“志量豪迈,英风伟略,冠绝一时”。1920年以后,他先后任呼伦贝尔善后督办公署咨议、黑龙江省督军公署咨议、全蒙联合总会副会长、北京政府参议,并被封为辅国公。
凌升自担任上述职务以后,强调民族及地区特点,主张重牧轻农方针。他建议东北地方当局采取措施,约束关内大批农民无节制地移入这一地区,制止军警廉价征购大批役畜和畜产品。为防止匪患,减少当地驻军对牧区的扰乱,减轻苛捐杂税,他经常奔走于海拉尔与齐齐哈尔之间,为稳定这一地区做出了贡献。这一期间,他又先后任“蒙疆”经略使顾问、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东北保安总司令部顾问等。1928年,他又任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 1929年,中东路事件发生,苏联红军进驻海拉尔,海拉尔成立地方治安维持会,凌升出任会长。这一事件解决后,苏军在撤退前与凌升商定:一旦苏日发生战争,呼伦贝尔应向苏靠拢。“满洲国”成立后,日方曾向凌升询问有无此事,被凌升一口否认。但此事引起了日方的注意。
1931年“9·18”事变发生后,因其对即将成立的“满洲国”抱有幻想,曾到抚顺“劝驾”和参与“建国”活动,是“建国元勋”。“满洲国”成立后,凌升出任兴安北分省(后改称兴安北省)省长。但是,他的幻想很快就破灭了。随着日本加紧实施吞并中国东北的侵略政策和步伐,从党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机构都委派掌握实权的日本官吏,他们名义上是“参事官”、“顾问”,实际上都是发号施令者,是“太上皇”。凌升在逐渐看清日本人的本质后,决心不当傀儡。在省公署内,凡是不通过他批准的事和签发的文件,一律不予承认并宣布无效,这使日本“参事官”非常尴尬;对日本人不惟命是从,坚持己见,甚至连关东军派驻海拉尔特务机关长的话也不听。因此,日本人视其是“不老实的人”。
1935年6月,以“伪满”为一方,以蒙古为另一方的“满洲里会议”召开,会议的主题是“哈拉哈庙归属”问题。凌升以“伪满”首席代表身份与会,但他却没有自由发言权,发言内容要由名为代表实为日本特务机关长的斋藤正锐决定。凌升对此极为不满,提出异议并与斋藤发生争辩。
1936年3月,“伪满”在新京(长春)召开兴安四省省长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凌升对日本关东军制定的“满洲国”“国策”进行了猛烈抨击:反对日本的“土地奉上”和向兴安四省派遣日本开拓团的计划;不同意将日语作为“满洲国”的“国语”;反对日本官吏把持蒙旗实权;反对把内蒙古东部地区划为兴安四省。他在会上气愤地说:“我在旅顺时曾亲耳听板垣说过,日本将承认‘满洲国’是个独立国,可是后来事实上处处受关东军干预,我在兴安北省有职无权,一切都是日本人做主。”凌升的这些话弄得主持会议的日本官员怒不可遏。他们无法忍受凌升对日本侵略者的既定“国策”的攻击,如果任其下去,后果将非常严重,因此下决心除掉他。
另一方面,当时,驻守海拉尔的日军骑兵集团长笠井等为了掩盖其在“满”蒙边境冲突中屡遭失败的责任,声称有人通苏通蒙,窃取日军行动情报,致使日军惨败。于是在“满洲国国境”附近逮捕了兴安北警备军上尉团副沙德勒图和兴安北省警务厅警尉倭信太。日本宪兵严刑拷打,逼迫他们供出背后的关系,由此制造出了凌升等有间谍活动和“反满抗日”、通苏通蒙的口供。
为防止凌升部下和兴安北省少数民族的反抗,还在会议期间的3月下旬,日本军方开始在海拉尔、索伦旗南屯、西屯和莫和尔图等地戒严,由日本特务机关和日本宪兵逮捕凌升的亲信及部下20余人,其中主要有:兴安北省警备军上校参谋长福龄(凌升胞弟),兴安北省警务厅厅长春德(凌升妹夫),兴安北省总务厅总务科长双海,会计科长葆定,索伦旗公署行政科长额尔很巴雅尔,新巴尔虎左翼旗警务科长春海,新巴尔虎右翼旗警务科长拉玛迪,海拉尔市政管理处顾问梶原(朝鲜族)等;被革职的有:兴安北省总务厅长荣安,海拉尔市政管理处长德春,索伦旗长恩明,满洲里办事处长龙登布。3月29日,凌升由新京返回海拉尔,下车后即被日本宪兵队逮捕,一同被捕的还有他的秘书官兼日语翻译华林泰。
日本宪兵队逮捕凌升后,立即搜查他的住宅和旧副都统署,搜出存放在副都统署仓库内的两挺机枪、50支步枪和数万发子弹。这些枪械子弹是苏炳文退入苏联之前留下的,凌升等尚未正式转交给警务厅,所以成为凌升等通苏的证据之一。
凌升等人被捕后,在海拉尔日本宪兵队队部受到严刑拷打,但他们谁也没有承认日本人所罗列的罪状,没有供出任何“通苏通蒙”的事实,也没有连累其他人。在拷问中,凌升一人承担责任,说:“别人无罪,都是我一人担当,不要牵涉别人”。4月12日,凌升等6人被移送新京(长春),在军事法庭上,他们仍未承认任何罪行。
4月14日,凌升等人被褫夺勋章与纪念章,“满洲国”政府方面公开发表了所谓“兴安北省各要人私通苏俄内幕”及“凌升被免职惩戒”的消息[1];4月19日,发布《凌升等通苏通蒙公报》,判处凌升等人死刑。4月22日,“满洲国”政府军政部发表了凌升等人所谓“企图蒙古团结独立,阴谋叛乱危害国家”[2]的“通苏案罪状”。其中提到:“凌升于民国十八年(昭和四年)苏中冲突之际在海拉尔会见苏军司令官奥斯托里希夫,对于蒙古独立,确定将来由苏联给予决定性的援助。后来,通过驻海拉尔的苏联领事和海拉尔火车站站长,收集提供情报,企图伺机内外蒙古独立。(昭和)十年六月作为首席代表出席满洲里会议时,与外蒙代表秘密联络,达成采取行动的协定。还在省公署内的传达室召开秘密会议。尤其是敖兰呼都格事件之后,将日满军国境警备部署事先通知苏、蒙军”。[3]
4月24日,凌升、福龄[4]、春德[5]、华林泰[6]等4人在新京南岭惨遭杀害,沙德勒图[7](达斡尔族,郭博勒哈拉)、倭信泰[8]两人被分别判处15年、13年徒刑,其他人则在被监禁几个月后被革职、停职。
在凌升等人被害前,其家人应召去新京监狱会见。他们已知道将要被杀害,但仍很坚强。临别时,凌升跪在地上,叩拜老父贵福。凌升在狱中曾用满文书写千余字的遗嘱,大意为,我被日本人所害,是因为保护地方利益,故引起他们的不满和仇恨。凌升等人被害后,目睹行刑的伪治安部官房长官入江上校回忆说:“这人真倔强,临刑时面不改色,含着冷笑。叫他戴上覆面时,坚决不戴,挺着腰极不在意。问他还有什么说的,他说没有,快打吧!”
凌升被害后,其任特任官的老父贵富被撤职,在哈尔滨学习俄语的儿子色布精太[9]被迫中途退学转入东京兽医高等学校。
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拟将查抄没收的大量凌升家产充做伪蒙古自治军的军费,遭到时任伪蒙古自治军总司令德穆楚克栋鲁普的拒绝[10]。日本关东军还以凌升有“反满抗日活动”,逼迫时任伪满洲国皇帝的溥仪解除了其妹与凌升儿子的婚约。此外,借凌升“通苏通蒙”事件,根据伪满蒙政部的指令,除前文提到的双海、葆定等人外,对兴安北省公署内的凌升亲信和关系密切者共20人进行“整顿”(实际上是清洗),以5月31日为限,发给两个月的工资作为退职金处理。同时,换上由此空出职位的日系官员。 [11]
所谓的“凌升通苏事件”,无论是当时还是以后,都是不存在的。这是日本关东军的一个重大政治阴谋,即对内加强统治、对外防止内蒙古东部地区蒙古人(泛指少数民族)的“离满倾向”,进而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日本关东军不择手段,亦不管你是省长、“开国元勋”,父亲是“满洲国参议府参议,甚至与溥仪有姻亲的关系,只要敢说日本的不字,不听话,即可给你安个罪名处死。他们的目的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达到了。
作为一名旧官吏,作为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凌升曾维护过封建统治,但他最终作为一名有民族正义感、民族气节和维护民族利益的爱国人士、少数民族代表而受到后人的尊敬。他为呼伦贝尔现代史上反抗外族欺侮和帝国主义侵略书写了光辉的一页。
1995年,居住在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托海镇的达斡尔族离退休干部、在职人员和群众(以敖拉、郭布勒、莫日登三姓为主)召开会议,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缅怀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中殉难的抗日志士。会议决定,以集资的形式,在镇内公园修建“抗日殉难志士纪念碑”,纪念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殉难的凌升、福龄、春德、华林泰等12名爱国志士。次年9月3日,在南屯公园举行纪念碑落成典礼。2003年8月,在旗人民政府的支持下,重修纪念碑,并改名为“抗日志士纪念塔”。现在,它已成为鄂温克族自治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
注释:
[1]1934年4月14日《盛京时报》,金海著:《日本在内蒙古随民统治政策研究》,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2]1934年4月23日《盛京时报》,金海著:《日本在内蒙古随民统治政策研究》,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3]《凌升通苏案件概要及军法会审判决》,1938年,国民资料编汇所,转引自日本蒙古友好协会编《蒙古入门》(日文),东京,三省堂,1993,第253页,见《日本在内蒙古随民统治政策研究》,金海著,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4]福龄,凌升胞弟,字松亭,生于清光绪十五年(1889),内蒙古鄂温克旗人。早年就读于呼伦贝尔八旗学校和齐齐哈尔中学,曾任索伦右翼正黄旗骁骑校、额鲁特旗总管兼呼伦贝尔保安队统领等职。1925年10月,以呼伦贝尔地区代表身份出席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张家口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此后,由于种种原因,他与郭道甫、福明泰等人分手。1930年,与春德等6人作为呼伦贝尔和东西布特哈地区达斡尔族代表,出席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的有关蒙古盟旗制度和自治问题的蒙古会议。1931年日本发动“9·18”事变后,福龄随其兄参与伪满洲国的“建国”活动。伪兴安北省成立后,任伪兴安北省警备军上校参谋长。凌升被逮捕后,福龄硬拉着伪兴安北省警备军顾问寺田利光到海拉尔日本骑兵集团笠井平十郎中将那里,以强硬态度提出抗议,被日本宪兵队逮捕,遭到严刑拷打,逼其承认“通苏通蒙”,被拒绝。4月24日,与其兄一起被杀害,终年47岁。
[5]春德,凌升妹夫,字子馨,达斡尔族,敖拉哈拉,生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内蒙古鄂温克旗人。曾任小学教员、呼伦贝尔副都统署笔帖式、奇乾税务局长。1929年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会委员,次年以呼伦贝尔地区代表身份出席在南京召开的蒙古会议。“9·18”事变后回到海拉尔,任伪兴安北省警务科长。1935年6月以随员身份参加边界问题“满洲里会议”。不久,任伪兴安北省警务厅长。1936年4月因凌升事件被日本关东军杀害,终年42岁。
[6]华林泰,字泽吾,达斡尔族,敖拉哈拉,生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内蒙古鄂温克旗人。曾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经济学,参加郭道甫组织的呼伦贝尔青年党,通晓满、蒙、汉、日、俄、英语。1925年10月出席在张家口召开的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后,被推荐为冯玉祥将军驻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1926年访问苏联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1928年7月,参加由郭道甫、福明泰发动和领导的呼伦贝尔青年党暴动。“9·18”事变后,任伪兴安北省公署首席秘书官兼省长凌升日语翻译。1936年3月底与凌升一同被捕,同年4月被杀害,终年39岁。
[7]沙德勒图,达斡尔族,郭博勒哈拉,生于1914年,内蒙古鄂温克旗人。曾任伪兴安北省警备军骑兵7团上尉团副。1936年4月因凌升事件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受到严刑拷打,被判处15年徒刑,关押在抚顺日本陆军监狱,两年后死去。
[8]倭信泰,达斡尔族,敖拉哈拉,生于清宣统元年(1909),内蒙古鄂温克旗人。曾在海拉尔蒙旗学校读书,参加1928年呼伦贝尔青年党暴动。“9·18”事变后,曾任伪满洲国皇宫卫队队员,1934年任伪兴安北省国境警备队警尉巡官。1936年4月因凌升事件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受到严刑拷打,判处13年徒刑,关押在抚顺日本陆军监狱,两年后死去。
[9]色布精太,凌升之子,生于1914年,曾入呼伦贝尔蒙旗中学学习,伪“满洲国”成立后任溥仪宫内府侍卫官。新中国成立后,任海拉尔市政协2~8届副主席,1980~1984年任海拉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88年7月病逝。
[10]德穆楚克栋鲁普回忆说:“1936年旧历正月十八日,在我旗举行伪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典礼后不久,田中隆吉又来我旗,商洽扩编军队之事。提到所需经费时,他说:‘蒙古统一指挥机构已经成立了,亟须筹措经费,现在兴安北省省长凌升因通苏案被捕,听说他的财产很多,可以没收他的财产,作为军政府的军费。’我当即拒绝说:‘凌升被捕,对于蒙古人心和西进工作都有影响,最好不要严究,应当从宽发落。至于我们所需经费,可设法另行筹措,绝不愿把没收凌升的财产充作我们的经费。’田中隆吉见我不但不愿接受这样来路的筹措经费,反有营救凌升之意,立刻转了话锋,向我解释说:‘凌升虽然被捕,我想康德皇帝出头一说,也就没事了,希你放心。’谈至此,他即告辞而去。同年4月24日,在锡盟乌珠穆沁右旗召开伪蒙古大会,准备正式改元易帜,成立伪蒙古军政府,当时我和索王、卓特巴扎普、吴鹤龄提出以大会全体代表名义,要求释放凌升,预定关东军代表到达后,即提出这一问题。在大会进行中,日本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横山须等赶来参加。刚下飞机后,吴鹤龄就将大会准备给关东军打电报,要求释放凌升情形,向田中隆吉等报告。田中隆吉答复说:‘时间来不及了,大概今天就把凌升处决了。’接着他到屋里又继续解释说:‘对处决凌升,本来我是不同意的,在关东军参谋会议时,曾讨论处理凌升问题,我这主管蒙事的参谋主张不杀,把前次你和我说的应当从宽处理凌升,以免影响西进工作和蒙古人心之言都说了。但是主管关于苏联事情的参谋都主张杀,最后实行表决,我是少数,只有服从多数,结果就决定把凌升处以死刑。这是我们内部处理凌升的经过情形,我都明白地告诉你们’。我们听他说明以后,认为既已把凌升处决,没有再向大会提出这一问题的必要,仅在会外时间告知了大家。索王、卓特巴扎普等,都和凌升有交情,闻听之后,不胜叹息。嗣后陶克陶向我说:‘田中隆吉和横山顺闲谈时说,杀凌升的事,对西蒙人的印象很不好。’”(见党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华北事变》,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643~645页。)
[11]见吉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历字315号全宗7号目录689号卷第85~90页“海宪(高)第四十六号《关于整顿兴安北省蒙系官吏的反响的通报》·昭和11年5月30日·海拉尔宪兵队长、警务部长板尾秀一”。
(作者: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档案史志局)
- 年鉴刊物上一篇:【书画摄影】包巴特尔摄影作品
- 年鉴刊物下一篇:【志鉴论坛】地方志工作法制化探究
- 声明: 转载请注明来源于《内蒙古区情网》官方网站














 当前位置:
当前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