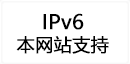第一期
- 【史海钩沉】尘封的历史——记喜扎嘎尔旗
- 【史海钩沉】20世纪30年代绥远省考选县长
- 【史海钩沉】什拉乌素壕村的天主教堂
- 【史海钩沉】丁道衡发现白云鄂博铁矿
- 【导读】本期导读
- 【特载】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志办公室2013年工作要点
- 【志鉴论坛】深入进行方志性质理论研究
- 【志鉴论坛】第二轮志书概述纂写浅议
- 【志鉴论坛】关于志书对会议记述的探讨
- 【专稿】额济纳出土的居延汉简
- 【专稿】草原护羊英雄——道勒格亚
- 【志书评议】乌兰牧骑精神永载史册——读《翁牛特旗乌兰牧骑志》有感
- 【文化博览】安代舞的传奇故事
- 【文化博览】文物收藏与鉴定的现实意义——以书画的收藏和鉴赏为例
- 【大事记】内蒙古大事记(2013年1月~2月20日)
- 【书画摄影】瓦·哈斯摄影作品欣赏
- 【珍珠滩】三道桥的老味道和其它——试图读懂一座古城的前世今生
- 【珍珠滩】灯笼河牧场的名片
- 【书画摄影】思飘云物外 诗入画图中
- 【志鉴动态】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志办公室举办《内蒙古年鉴》撰稿人培训会议
- 【志鉴动态】《磴口县志》(1988~2010年)(稿)评审会举行
- 【志鉴动态】《翁牛特旗乌兰牧骑志》出版
- 【志鉴动态】《阿鲁科尔沁旗志》(1989~2006年)出版
- 【珍珠滩】三道桥的老味道和其它——试图读懂一座古城的前世今生
- 发布时间:2013-12-30
- 来源:本站原创
● 题 记
巴彦浩特三道桥回民食堂打的茴香饼子,那种三角形的,长方形的,烤得的金黄酥脆的,老远就能闻见纯正的面香味茴香味。
这么多年过去了,许多人还惦记着那个味道,和弥漫在三道桥头的家乡气息、乡音里夹杂的踏实中的寂寞,和淡淡的乡愁。
早些年,一链子又一链子大膘煽驼就是从三道桥悠闲地走过,坐在桥头栏杆旁喝酒的人也不是没有。
真的,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味道,迥异的,个性的,不可重复的。
三道桥,就是“塞外小北京”的王府井,乃阿拉善盟盟府巴彦浩特第一繁华地。逛过三道桥,你就算来过巴彦浩特了,来过阿拉善了。
1
三道桥名声在外,阿左旗人离开家多远,想的就是在三道桥头悠闲地走来走去的感觉。本土人士做生意是不需要吆喝的。你去三道桥、新华街、开元门口或转盘,也听不到什么吆喝。偶尔有个把轻声低吟的,你一听口音就知道刚从外地来,不懂规矩,不懂路数。
也有个例。
或长长的一声,怪吓人的,听不懂喊什么,只有拉着拣破烂的小车,告诉着你,他是异乡客。
间或还能听到一声凉州腔:子麻撂?让人忍俊不禁。
或短短的喉音,羊皮——自行车上后架捎着一张还滴着鲜血的山羊皮或绵羊皮,用喊吗?
默默的三道桥,用恬淡概括了一个又一个不事张扬的日子。
雨是一年年少了,街上的车是一天天多了,多的不可思议,若过江之鲫。
巴音是个平和、踏实、淡定的小城,人们走路平和、说话平和,街上也很少能看到打架吵嘴的。没有时下许多城市的浮躁。那里人的火气很大,说话很冲,在嘴上也不愿吃一点亏,整天的活儿就是捣搅,也叫折腾,声音雷式吼呢。
小城一代一代繁衍着。
不过,我还是喜欢当年驴马粪、烧酒味、汗腥味、青秸味混杂的味道,怪怪的,淡淡的,纯纯的,近乎自然的。
人嘴寡了,上火了,要一盘南梁坡的沙米凉粉,油汪汪的,芥末冲鼻,刺击口条,进了肚子沁凉沁凉的舒服。左旗女人几天不吃此物,心理便空落落地没爪挖。
2
巴彦浩特,当地人和周边人称巴音,约定俗成了,叫了多年了。
巴音,冬暖夏凉。
七月流火,而巴音的夏天却有点儿沁凉,时不时还滴几个雨豆子,抑或雷声在点缀我们的生活。偶而有几个晚上,盖被子还有点儿凉呐。
因此,这里居民安空调的不多。还说什么,爱自然风,环保云云。
三道桥的街心花园,三羊开泰雕塑旁,成了纳凉休闲的好去处,人们一边喧荒,一边看景,一边看人,甚至一边等生意,那可叫守株待兔了。女人成了夏天的风景。她们怕热,打着阳伞,穿着短裤、短裙、吊带装,用五颜六色和色彩纷呈装点着七月的巴彦浩特,满足着自己的眼睛和别人的眼睛。有的女人上街,什么也不为,只为转转,看看,展示一下自己,逛街是女人的天性。
“你在街上看景,人们在街上看你”,不知是谁的一句,为这一切找到了理由。
现在三道桥,围着它转的多是南来北往的民工,还有些掀花花、挖牛九的老爷子,其他人都是过路的,只是看几眼红男绿女,闻几鼻子美味佳肴,如此而已。
3
三道桥已不是过去的三道桥,桥面被铺得很宽,不知底里的人已看不出这里曾经是座桥。河已成了暗河,任上游泄下的泉水雨水从暗河悄然流过,流向健康湖,流向西关村的农田,甚至头道沙子里。
早年先的三道桥,河水如练,清澈透明,潺潺流水,河边长满碧绿如洗的青草,任牛羊鸡狗们嬉戏啃食。小河的流水亦可直接饮用,小孩渴了捧起来就喝,凉凉的,没听说谁闹肚子。
中国著名诗人李季曾经来到小城,看着小桥流水,不由诗兴大发,挥笔写下了:有三条清澈的小河,从巴彦浩特流过/有三个穿红衣裳的姑娘,从沙漠到北京去上学/有三条清清的小河,哺育我们的牛羊骆驼……这些在现在看起来不称其为诗的诗,在当时亦轰动一时,提高了巴音的知名度。三道桥既不是政治中心,又不是经济中心,它只是像北京的天桥,呼市的南茶坊,银川的南门,兰州的西关什字,是老百姓聚集的地方,草根文化的发祥地,你要想了解定远营,了解古城的文化,就首先要读懂三道桥。
那些年,牧民进城,是拉着大膘骟驼从三道桥上旁若无人地走过的。最不济,骑上个毛驴也照逛王爷府,精精神神的。
吃一碗瓦罐里卖的羊杂碎,便滋润了,便踏实了,那可是巴音的标志性小吃吆。而沙米调和,则是沙米、碎面、土豆、羊肉丁的混搭,动、植物的诗意融合。入口,充满了滋润和舌尖的快意,这实在是口条上味蕾惹的祸,让吃货们有了说头,说什么,几日子没吃,心理干焦干焦的。另外,要就上腌沙芥,呛鼻子的那种,这就全乎了,就滋润了。胃是有记忆功能的,小时候吃惯什么,一辈子都改不了,我就是这样的,且梗顽不化。
常感慨,那种烧得黄亮黄亮、焦黄焦黄的羊头怎么就吃不上了。药水涮毛一摆就白净白净的那种,谁敢吃呢。至今,我都在苦苦寻找那种炭火柴火上烧的本地羊的羊头,予备着大块朵颐一番,羊脑子是断不可少的,本人好的那一口吆。
现在,人们青睐火锅子。我想,这和河套大烩菜有异曲同工之妙,区别在于,一个在餐桌上操作,一个在肚子里交融。
4
小地方,人们见了面,对了眼,脸儿都熟,跟谁都能搭上话。
也就是在这座西部内陆腹地的沙漠小城,一样有特色。有街逛、有小吃、有红火,有想头、有盼头,这就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是当地人在这里人生存、守候、繁衍的理由。
三道桥,四季都有不同的味道,不同的景致。
每年初秋,贺兰山的紫蘑菇白蘑菇就如期成为三道桥的一道时尚风景,一筐一筐,散发着浓浓蘑菇的香气。早年间一斤,才一两块钱,时下,已卖到20多块了,还在涨。
到了春天,沙葱便先是星星点点,最后是一堆一堆的,卖的多,买的也多,从十几块钱吃到一块,再从一块吃回到十几块,甚至几十块,无论贵贱都有人买,不过几毛钱的沙葱你是永远吃不到了。沙葱是跟着雨水走的,一场雨水一场绿,左旗人右旗人下饭离不了沙葱,没有沙葱再好的饭也吃不香;血肠里不掺沙葱,再好的血肠也不正宗,腻腻的,总觉得缺少什么。
一到秋天,邻近银川人的必修课是晒辣子,左旗人是腌沙葱,买光了街上的大缸小瓮,到处打问哪儿卖腌菜的大颗粒盐,仿佛只有腌了沙葱才能过冬天,女人才是过日子的女人。
一缸绿油油的沙葱,是这家女主人的名片和炫耀,客人来了端上来,女主人脸上有光,有面子。
夏天,沙米凉粉、茄辣凉面,让你前心凉在后心,爽死了。
而冬天,则是该大啖肥绵羯子的时候了,两指厚的油,白是白,红是红,煮羊背子,吃茶泡肉,是好不过了。
我始终认为,左旗人吃的很固执,很一根筋,对待羊肉的至死不渝和一往情深。从你吃羊肉的架式和最后羊骨头的结局我就能判定你是老巴音还是新移民,
最是那根光洁的羊棒骨,操刀者只须用刀背精准地敲击,骨头便神奇地断裂,此公轻取骨髓,淡然食之,谓之吃家子,谓之游刃有余。
老百姓有老百姓的活法,我始终认为酸奶子干饭就沙葱和羊肉揪面就是阿拉善平民饮食文化的精髓和基本元素。
不由凑上一首小诗凑趣(范伟体):才饮酸奶子,又嚼酪蛋子,千里沙子任行走,肥羊羯子最顺溜,一口酒,一口肉,数点驼城众多景,尽享美食亦风流……
5
走在三道桥上,三道桥的桥虽然已经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地理位置和一个地名符号。原来桥头的露天市场已搬进了两层彩钢大屋顶的市场,进了屋子的市场已没有了原先市场的味道和气氛,人为的痕迹很重。菜的颜色菜的鲜嫩在顶棚鲜艳的背景色中难以识别真伪,很容易看走眼。
从20世纪80年代,三道桥就是阿盟最大的农贸市场,成为驼城一景,也是我最多、无数次光顾的地方,为的是开开眼界,解解心荒,看看红火。常走的路径是先逛市场,再进驼城大厦(现在的驼旺),再沿着新华街走几个店(新华书店绝不可少),巴彦浩特也就转得差不多了,该看的也看了,该买的也买了,该问的也问了,回吧。桥南头有个副食门市部没去(旁边是副食品厂),老巴音人都爱在那里打酱油买醋,还有茶叶,上好的茉莉花茶才20多块钱一斤。现在也拆迁了.老住户们唏嘘感叹了许久:“这醋以后去哪儿买呵,袋袋醋反正我们是吃得没味。”
现如今,开元、进来看超市让人们把当年的驼城、驼旺淡忘了,更不要说祥泰隆了。
那年,给我印象很深的还有一件事是,某一天三道桥小吃市场开张了一家牛肉面馆,那可是巴音历史上真正的第一家,听老板口音好像是甘肃人。时间大概是1985年,或再早一点。这家的牛肉面虽不能说是一清二白三红四绿,却香透三道桥,食客闻味而至,生意红火得了得,吃惯羊肉烩削面的巴音人换了个胃口。我在兰州上大学时好上了这一口,隔三岔五便要狠吃一顿。去了坐下依然一声断喝:二细,加肉!听这口气,老板就知道吃家子来了,不敢怠慢。大约过了一年天气,不知什么原因,牛肉面馆便歇业了,我也断了吃牛大碗的路子,惆怅了许久。我现在都为这家牛肉面老板叹息,如果开到现在,那可大发了,三五十万算是小数,怎么就不开了呢?可惜了这个绩优股。
6
还要说一下岳钟琪将军,早先我一直以为他仅仅是定远营第一任城防司令,差矣。
最近一睹《甄嬛传》才知道此公乃赫赫川陕总督,封疆大吏,亦与巴彦浩特结下了不解之缘。岳钟琪于1730年(清雍正8年)奏建定远营,次年,将装修好了的城池奉旨赐于阿宝,并写下了雄视千古的名篇《定远营记》,以昭示后人。
那时,就是岳大将军,一眼看中的就是三道桥,还有八卦泉和营盘山,完成了阿拉善历史上第一个城镇化进程。
现在你站在营盘山鸟瞰,不由叹服这位文可安邦,武可治国,满腹经纶的大将军是何等的远见卓识。
风调雨顺,易守难攻是岳钟琪将军建造定远营古城的基本思路。
7
从三道桥往南,便是南梁坡了,那是一个隆起的高度,见证了一座城市的荣辱兴衰、地域斯文和人脉特质。
阿盟一中矗立在那里快一个世纪了,是这片2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最高学府。不由想起那座窄窄的简陋的青砖砌成的校门,比现在的电动推拉门差好几个档次。然而我还是觉得那个曾经的校门更有历史的沧桑感,就像清华园一样,那是历史在某个瞬间的定格。我感叹南梁坡,那片芬芳的读书声。当年家兄即从这座校门走向国内著名学府,继而进入京城高端科研机构的。
走在南梁坡,想起住在附近一个姓李的老爷子,此公乃上世纪80年代三道桥回民食堂的大厨,掂炒勺,手艺了得,能打正宗的茴香饼子,能炒地道的葱爆羊肉,是阿拉善美食的见证人,亲历者。现在他赋闲在家,对我感叹道:“先前还给周围办事的人做个席什么,现在谁个还在家里做席呢,都进馆子了。”
8
当再次伫立三道桥头,那种巴音特有的气息,悠然的节奏,稔熟的乡音,还有我长长的等候,已经渐行渐远了,只有记忆还在。
皮子毛卖的也少了,头发菜更是难觅踪影。体育场西口夜市的红火市声,黄昏里的三道桥成为巴彦浩特最为悠闲的地方,让人淡定了许多,隐约有股鱿鱼加孜然的烧烤味飘来,不过我闻见的却是烤腰子,我的鼻子对羊的各部位尤其敏感。
南大街的轿车、出租车、摩托、电动车如过江之鲫,各显其能。一路二路中巴公交基本上是老头老太太闲人和民工的专车,他们一块钱也嫌贵。现在,四路、五路公交也开通了。不过,你要走个新中心医院、车管所什么,还挺费事,不知道坐哪趟车。
你要想吃发面馍馍,就去头道桥旁,有几个手推车上买,发面墩墩、炉馍、扇子都有,味道还可以,不过天阴下雨刮风就不出摊子了,买上买不上就看你的运气了。要吃正宗的,非山寨的,经典的,你就要多走几步去健康花园小区里的民勤馍馍店,篮球场旁边那家,老左旗人都知道。那可老正宗了,老好吃了,没放碱,没放发酵粉,没放添加剂,真正的纯天然。胡麻卷子、炉馍、发面墩墩、甜水馍馍、南瓜油果子、西葫芦包子,要啥有啥,门面啥时候都开着,是巴彦浩特发面馍馍第一店。旅游的,开酒店餐厅的,办红白事的,都从这里预定、拿货。游人离开巴彦浩特一定要給家人朋友带几个巴音健康花园的千层花馍,那个香嗷,那个地道哟。
总之,我对三道桥是情有独钟的,心存感激,甚至敬畏,他给了我太多。这里没有市声的喧嚣,没有涌动的车流人流,有着只有洁静宜人的空气和原生态的景致,和那些淡淡的乡情,那些操磨人的乡音的纠结丝然。
之于老味道老地方,走了还会回来,还会掉头,就是吃不够,这就是不舍,这就是牵你的绳,说不清,理还乱,舌头不会撒谎不会客气。
冥想中,朦胧里,三道河沟的溪水依然哗啦啦地流淌着,不紧不慢,不屈不挠,清澈的,棉软的,象女人的腰肢,我的心也跟着走了。
虽然我的性格很着急,但我心底却崇尚消停,一副恬淡从容的样子。
在三道桥头,我一眼就能看见定远营古城的城门楼子,一鼻子就能闻见定远营老味道的前世今生,进入一种境界,不知算不算时下的穿越。
我喜欢巴彦浩特的那种固有的味道,市井的,清冽的,青草的,暖暖的,还夹杂着羊肉烧酒的味道。是飘在三道桥头的那种淡淡的味道,稔熟的乡音,和消停的脚步,勾住了我的魂魄和口条、杂碎,我无语了,眼睛却先湿润了……
(作者:内蒙古作协副主席 内蒙古签约作家)
- 年鉴刊物上一篇:【志书评议】乌兰牧骑精神永载史册——读《翁牛特旗乌兰牧骑志》有感
- 年鉴刊物下一篇:【专稿】草原护羊英雄——道勒格亚
- 声明: 转载请注明来源于《内蒙古区情网》官方网站














 当前位置:
当前位置: